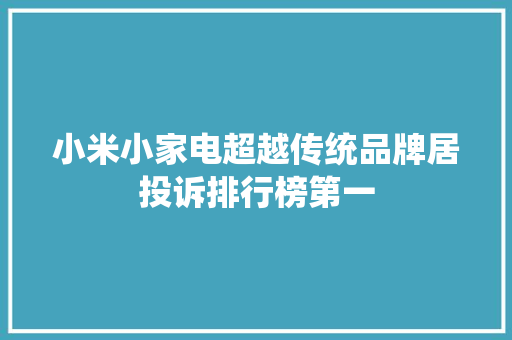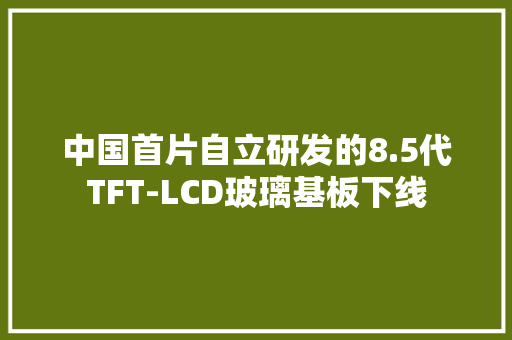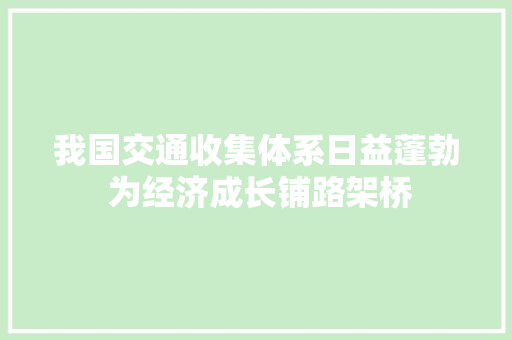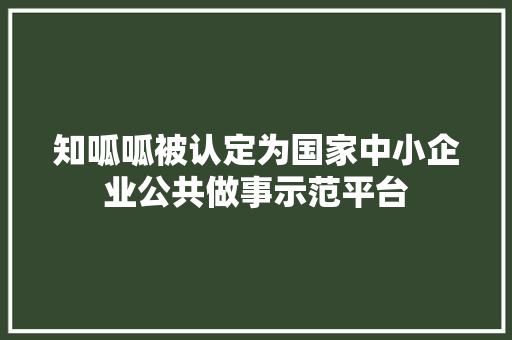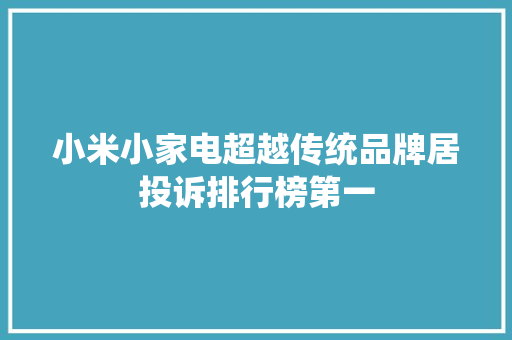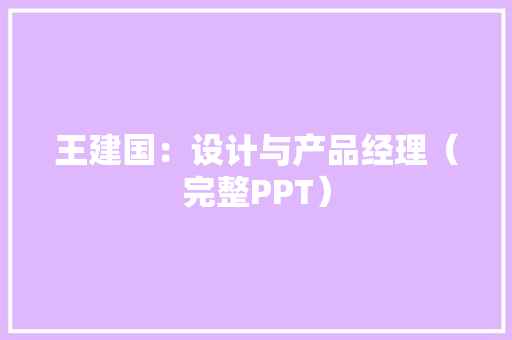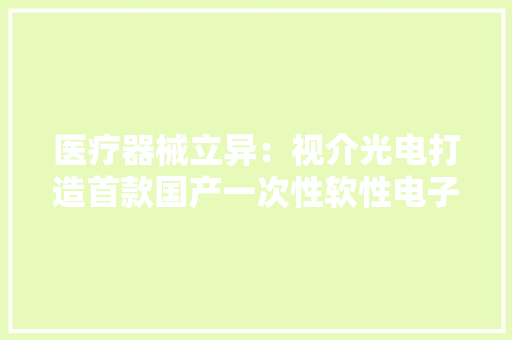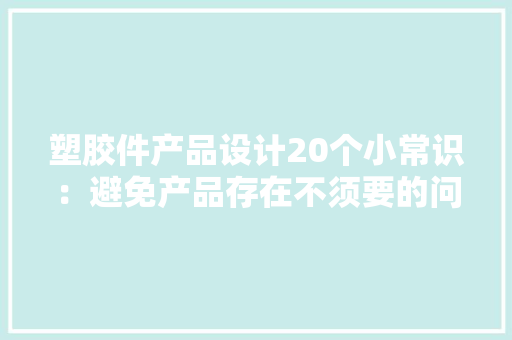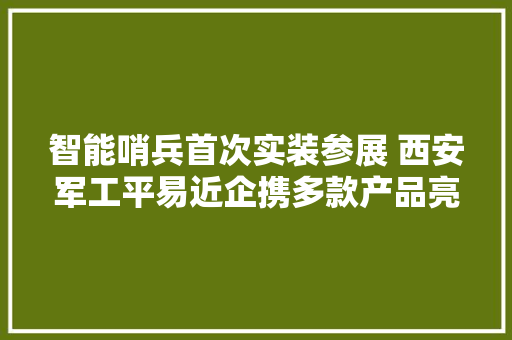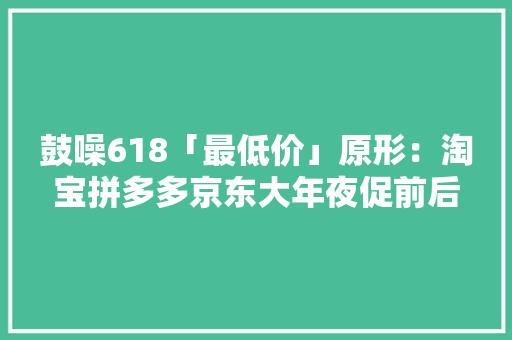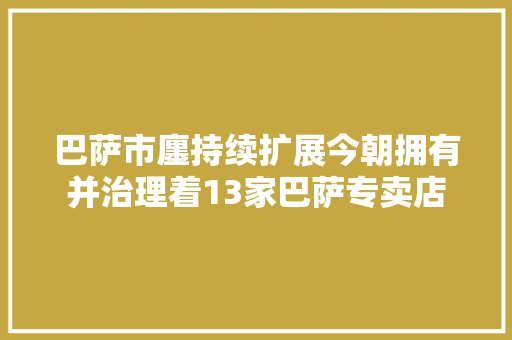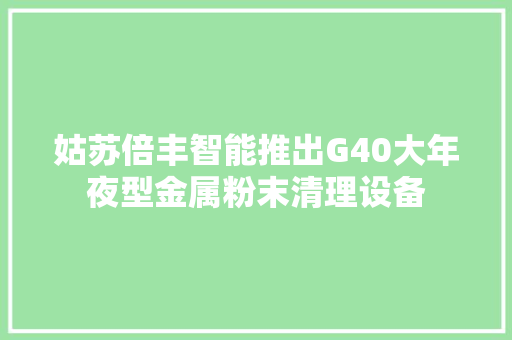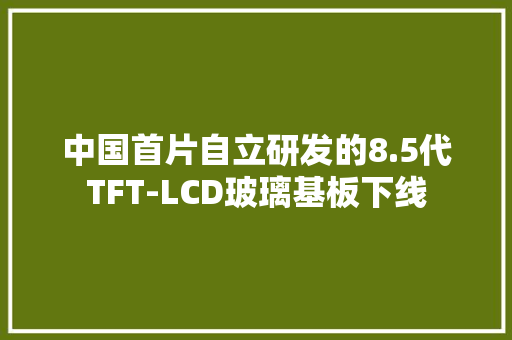这时王韶、李彻、李雄一班晋王府旧臣也俱已先后去世。杨广不失落机遇地将帮他谋夺太子位的一伙亲信拉进东宫任职。张衡为左庶子,杨约为右庶子,宇文述为左卫率,原督晋王府军事的参军段达为太子左卫副率,郭衍为左监门率,左仆射杨素蝉联朝中。后来在仁寿宫事变中将杨广推上天子位的,仍是这个当年帮他夺宗谋太子位的班底。只是杨素由于飞扬跋扈,引起隋文帝疑忌而疏远,仁寿二年(602)下敕,以“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为名,让他只须三五天去一次尚书省,评论大事,不再通判省事,“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杨约也远出为伊州(治今新疆哈密)刺史。这一变故反而匆匆使杨素全力支持杨广取代杨坚,在仁寿宫事变中表现最为积极。
仁寿四年(604)七月丁未(十三日),隋文帝去世于仁寿宫。乙卯(二十一日),太子杨广在仁寿宫即天子位。随即派杨约入长安,矫隋文帝诏,赐废太子杨勇去世,将他缢杀。隋炀帝弑父屠兄霸占皇位的说法盛行很广,在人们心目中几是定论。实际“弑父”一案,史料多歧异,还需考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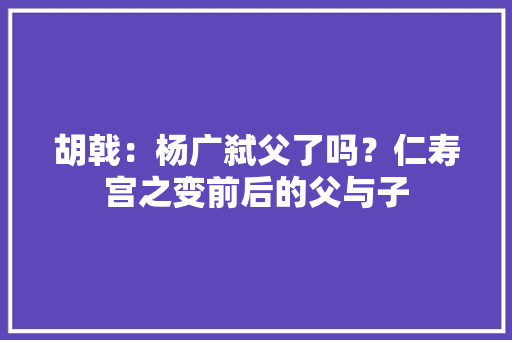
这一年的正月甲子(二十七日),隋文帝前往仁寿宫。行前,一个术士身份的预言家章仇太翼警告说:“但恐是行銮舆不反。”章仇太翼几次再三谏阻,是考虑隋文帝的康健,还是暗喻将生变故,已无法确定。此人虽目盲,但耳聪心明,彷佛有一点特异功能,“以手摸书而知其字”。前后所言都是政事,是个对政治形势心里有数的术士。他对隋文帝说的话,可算是一种政治讯号,隋文帝彷佛还很麻木,气恼地将他投入长安狱中,说回来时杀他。果真这次隋文帝一去不返了。

四月,隋文帝在仁寿宫罹病,七月甲辰(旬日)病危,“卧于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歔欷”。从容地与臣下告别,临终还没忘却交代太子开释章仇太翼:“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丁未(十三日),隋文帝去世在仁寿宫大宝殿,还留有遗诏,个中专门说了许多杨广的好话:“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勉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
上述《隋书》和《北史》的《隋纪》,所载隋文帝去世情形并无非常,也知道他的病因与耽于女色、房事过度有关,对此他自己有话交代:“使皇后在,吾不及此。”独孤皇后去世后,他与宣华夫人陈氏、容华夫人蔡氏等宠姬在一起,任情纵欲,毫无节制。到底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不到两年,就折腾垮了。当然上述材料中,遗诏的内容可作别论,由于遗诏每每是当事人弄虚作假的玩物,不一定能表达逝者的真实心声。
然而同是《隋书》,《杨素传》却又有这样的材料:
及上不豫,素与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入阁侍疾。时皇太子入居大宝殿,虑上有不讳,须豫防拟,乃手自为书,封出问素。素录失事状以报太子。宫人误送上所,上览而大恚。所宠陈朱紫,又言太子无礼。上遂发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谋之于素,素矫诏追东宫兵士帖上台宿卫,门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节度,又令张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颇有异论。
《北史·杨素传》所载与此完备相同。《资治通鉴》任命了这段史料,在“令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之后,加了一句“尽遣后宫出就别室”,补充了张衡下手的条件。再想到《隋书·张衡传》说张衡“临去世大言曰:‘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监刑者塞耳,匆匆令杀之”的情景,正史上已拐弯抹角地暗示了隋炀帝有弑父的劣迹。
野史条记的阐述便开门见山了。赵毅的《大业略记》说:
高祖在仁寿宫,病甚,追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唯陈、蔡二人而已。帝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曰:“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啮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庶人勇,即令废立。帝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简骁健官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仗,立于门巷之间,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马总的《通历》说:
上有疾,于仁寿殿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歔。是时唯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去世狗,那可付后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旁边,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
《通历》详述了杨素令张衡入室拉杀隋文帝的情形,只有《大业略记》明说指青鸟使是隋炀帝,他召杨素、张衡进的毒药。
隋代骑马女陶俑
现在看来,基本的情形是隋文帝对杨广的信赖一贯坚持到自己病危时。正月前往仁寿宫后,明天将来诰日便下诏“赏赐支度,事无年夜小,并付皇太子”。发病后又召他入居大宝殿,同自己住在一起。末了因杨广同杨素商量后事——恐怕还包括继位问题——信件的误传,犯了晚年笃信佛道鬼神的天子的大忌,隋文帝大怒之下想再改换太子,但来不及了。事发时,杨素一伙赶紧掌握了宫廷的警卫和下诏的职能部门,已经病入膏育的隋文帝随即去世于张衡之手。
只管可以一样平常地讲杨广参与了仁寿宫之变这场宫廷阴谋,但要说他父亲隋文帝是他指使杀害的,也便是确认他犯有弑父的直接罪过,材料只有《大业略记》供应的一条孤证,并不充分。而且就这条材料之中,别的书所说杨广调戏的宣华夫人陈氏,也改作蔡美人了,人名和身份——应是朱紫或径称容华夫人——都不对,手段也有进毒和拉杀的差异,因此其史料代价颇可疑惑。
考虑起来,仁寿宫之变的全部情节中,有无杨广调戏父皇侍妾之事,也有疑问。旧史都把太子无礼,宣华夫人反抗,因此被激怒的隋文帝决心换太子,当作引发事变的直接缘故原由。可是陈氏同太子的关系早就非同一般。她应是陈宣帝(528-582)晚年出生的女儿,此时不过二十多岁。她“性聪慧,姿貌无双”,隋文帝虽然最宠她,但她未必愿专注感情于这个六十多岁的“喜怒不常,过于屠戮”的老天子。青年漂亮的太子同她早有来往,“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事变之后,杨广立即派人给她送去同心结,她接管时虽然面有难色,还是羞羞答答地拜谢了青鸟使。“其夜,太子烝焉。”在父亲和丈夫未寒的尸骨旁,他们结成新欢。隋炀帝登基后也没冷落她。她去世时,“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从前前后后两人的关系看,当时在仁寿宫中发生太子施暴而陈氏激烈反抗之事,不大可能。况且受当时许多少数民族儿子合法地而且是有责任要继娶父妾习俗的影响,太子与父皇妃嫔之间发生些苟且之事,如李治(唐高宗)在东宫时与唐太宗秀士武则天有暖昧关系那样,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以是,纵然杨广有猥亵行为,陈氏也犯不着撕破脸皮跟他闹翻,为守住对那个行将就木的老天子的忠贞,而得罪这个已经跟自己关系很深的今后的靠山。当然,光凭理性的逻辑去推测历史是危险的,由于详细的历史过程,更多是由偶发的感性的成分推动的。特殊是女性的历史,紧急忙乱中她们更随意马虎损失理智犯糊涂。以是,我们对仁寿宫中有没有发生陈夫人反抗太子调戏一事,只存疑而不遽下结论为好。
在初步研究弑父的问题原形之后,我们想再谈论一下杨坚、杨广父子的关系。
杨广从前有“仁孝”或“大孝爱”的荣誉,对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那不一定是矫饰伪装。但按传统的标准衡量,杨广不是一个笃行孝道的人,连最疼爱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去世时,他也是“对上及宫人哀恸绝气,若不胜丧者;其处私室,饮食说笑如平常。又,每朝令进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鲊,置竹筒中,以蜡闭口,衣襆裹而纳之”。连葬礼期间忌荤食说笑的规矩都未曾遵守。所以为了一个天子位置,他即便做大不孝的事,也不敷为怪。
可是称帝往后,他又时时给已故父皇以各类高度评价,表示深切怀念。登基后,“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乃于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季致祭”。“夫孝者,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自天子达于庶人,虽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义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国家,化天下,故能不严而顺,不肃而成。斯实生灵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天经宫起名即取此义,将亡父的衣冠带往东都祭奠,表示炀帝的孝顺和以孝道求治化的决心,首创了一个深深影响唐代政治的传统。
“四季致祭”和“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似还嫌不足,大业元年(605)下诏议“月祭”:“高祖文天子,功侔造物,道济生灵,享荐宜殊,乐舞须别。今若月祭时飨,既与诸祖共庭,至于舞功,独于一室,交违礼意,未合人情,其详议以闻。”
大业三年(607)六月,再次下诏为隋文帝单独建庙,诏书盛赞其功业:
高祖文天子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册府元龟》作“黎”)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一车书。东渐西被,无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来苏。驾毳乘风,历代所弗至,辫发左衽,声教所罕及。莫不厥角关塞,顿颡阙庭。译靡绝时,书无虚月。韬戈偃武,天下晏如………高祖文天子宜别建寺院,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怀。
赞语用词无以复加了。
隋文帝泰陵
大业九年(613)闰玄月,隋炀帝从辽东回来,途经博陵(治今河北定州),不胜伤感地对侍臣说:“朕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年甫八岁,日月不居,倏经三纪,追惟平昔,不可复希!”他“言未卒,流涕呜咽,侍卫者皆泣下沾襟”。十月下诏,改博陵为高阳郡,“召高祖时故吏,皆量材授职”。
从上面这些材料可以透视到,隋炀帝内心仍保留着对首创隋王朝的父皇的敬爱之心。诚然他要祭起孝的旗帜来掩护自己的荣誉,但故意的造作和发自内心的真情,有时是可以区分开的。因此,对仁寿宫之变可否进一步作这样的判识:事出仓促时,张衡擅自或在杨素指使下戕害了病危中的隋文帝,当时还是太子的隋炀帝默认了,但他对此始终不能保持生理上的沉着。后来嫡黄花,腼腆与怨恨进步神速的隋炀帝,到底没让杨素和张衡善终,同时还用立庙祭飨等各类仪式,往返想亡父,借以后悔自己当年不慎的言行。
(本文摘自胡戟著《双面暴君:隋炀帝的平生、时期及原形》,岳麓书社,2024年7月。澎湃***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