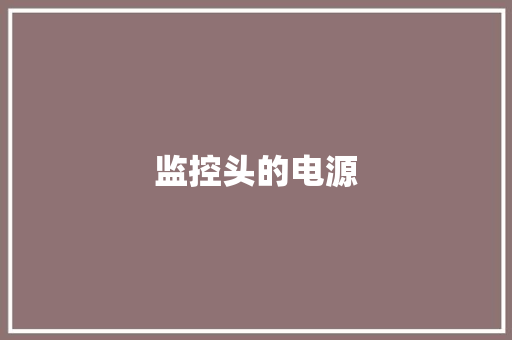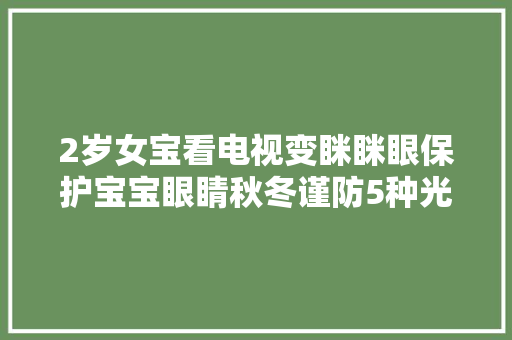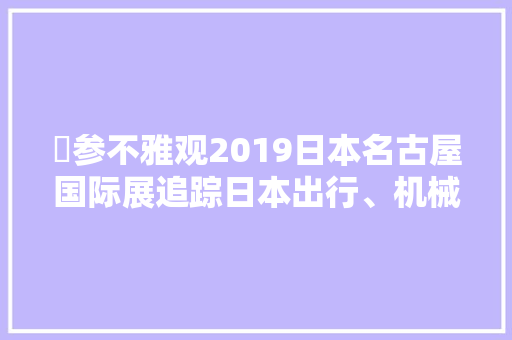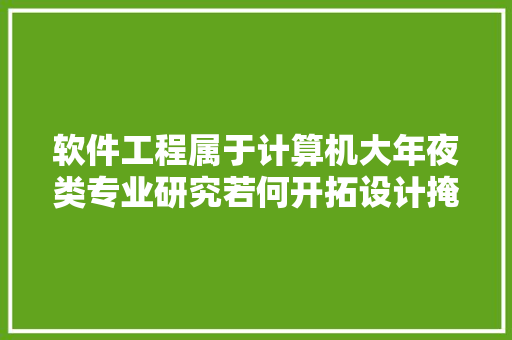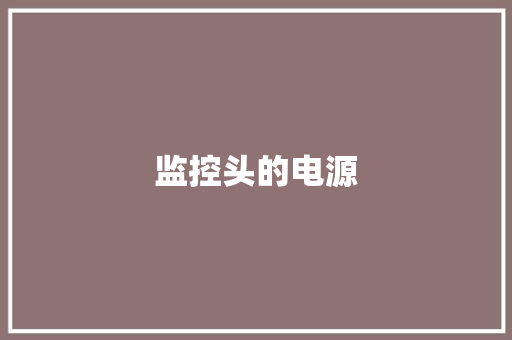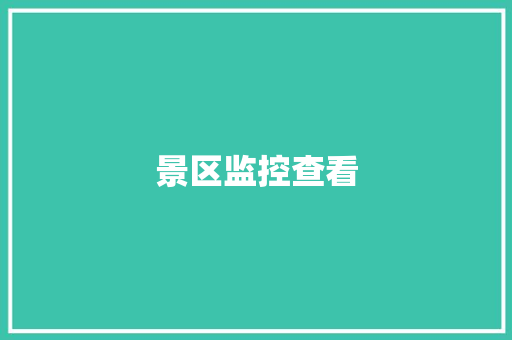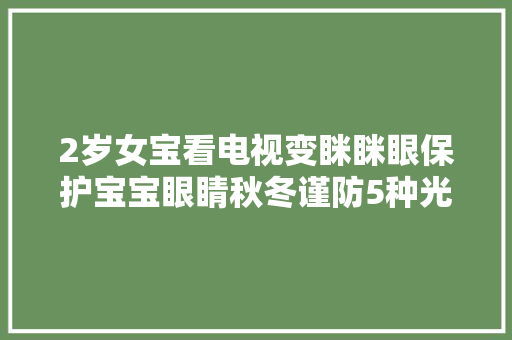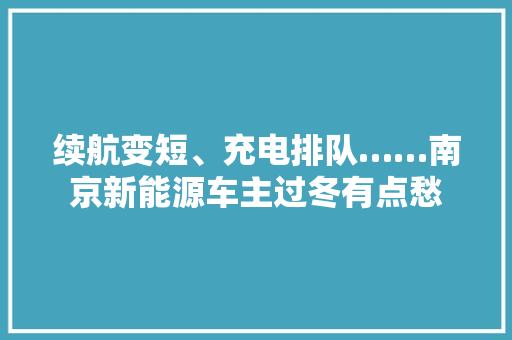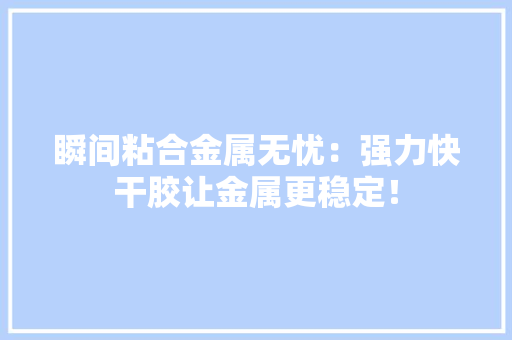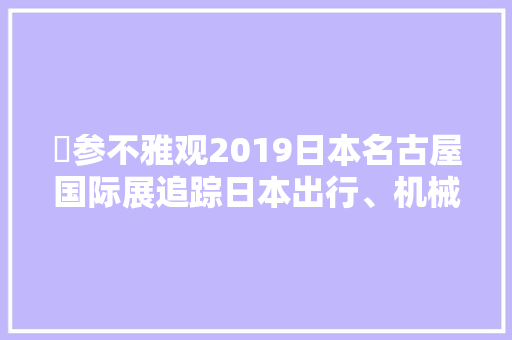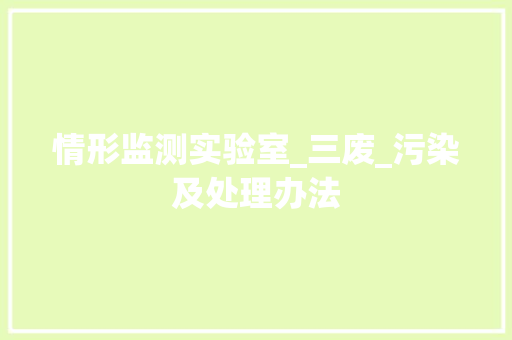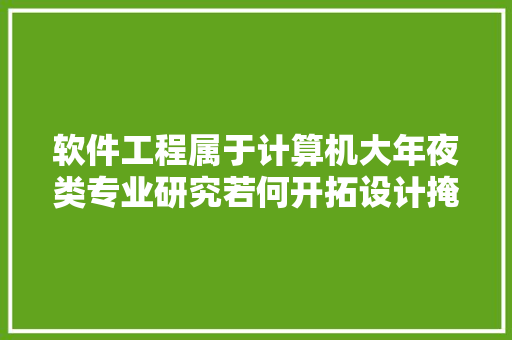“嘉靖说”最早,廿公跋已说“为世届时一巨公寓言”①,沈德符《野获编》指为“嘉靖间大绅士手笔”②,屠本畯也称“相传为嘉靖时”为陆炳诬奏沉冤者“托之”③。
及至本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吴晗始倡“万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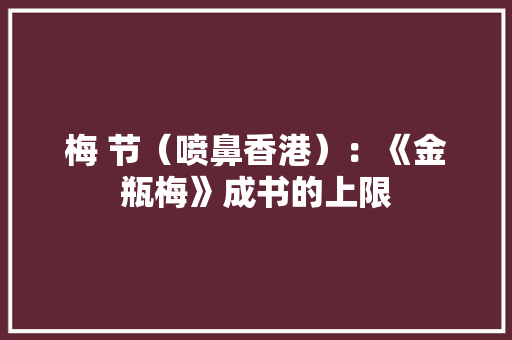
吴晗根据书中提到的一些财经、文化、宗教材料,如朝廷向“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佛教盛衰、寺人焰炽、小令盛行等等,断定“《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成书时期“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

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④吴说甚辩,然所据多属评估性社会资料,在韶光上颇有弹性,并不能完备推翻“嘉靖说”。
现在笔者也来凑个热闹,试图提出一些新的材料,看能否有助于办理这个问题。
《金瓶梅资料汇编》
一、“新河”凿成的韶光
《金瓶梅词话》本为“打谈的”的底本,这些说书艺人在淮安、临清、扬州、济宁等运河大码头上演唱。
明清两代,大运河是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国家财用兵食之所需,均取资江南,靠漕运转输。
但运河也是一条极薄弱的水道,既受自然旱涝的影响,更受黄河水患的侵扰。
统治集团为保持漕运畅通,花了弘大人力物力来管理运河。《金瓶梅》的作者对明代后期运河的情形相称熟习,书中的“清河”,应是运河边上的城镇。
《金瓶梅》虽“以宋写明”,但反响的运河是作者生活时期的运河而不是宋运河,《醒世姻缘传》的故事托始于正统、成化间,第三十回作者写宝光和尚从北京回常州原籍,却谓在“张家湾上了船”,“船过了宿迁,入了黄河”⑤。
运河从宿迁入黄,是明万历三十三年李化龙凿成泇河新运道往后的事,而这以前是在茶城和徐州。
我们据此可肯定,作者写此书时,必定在明万历三十三年往后。我们是否也可以从《金瓶梅》有关运河的描述,找出确定其写作年代的证据呢?
《金瓶梅词话》第六士六回,安忱以工部主事(正六品)督运皇木,一年届满,升都水司郎中(正五品),奉敕修理河道。
第六十八回过清河拜访西门庆,西门庆阿谀他“荣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略。河治之功,天下所仰!
”安忱却大呻河防之难:
“
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此民穷财尽之时。前者皇船载运花石,毁闸折坝,所过倒悬,公私困弊之极;而今瓜州、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带,皆毁坏废北(汜)。南河南陡(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
又兼贼盗梗阻,财用匮乏,大覃神输鬼没(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
⑥
”
载运花石,毁闸折坝,见本书第六十五回《宋御史结豪请六黄》,是北京末年故事,与明无涉。
但个中提到的“新河”和“南河南徒”,却大有干系。“新河”之凿成和“南河南徙”,都在嘉靖往后。
为讲清楚这个问题,先谈一下明中叶往后运河的变迁。
明清漕运,威胁最大的是黄河。从山东济宁至茶城一段运道,因靠近黄河,常因黄河东决而淤塞。
从茶城到清口五百多里运道,黄河也便是运河,一旦黄河决口,运道即“淤沙无水”。明中叶往后,河臣们逐渐认识到,要保持漕运畅通,就要只管即便避开黄河,实施“避黄走运”和“黄运分道”。
运河的改道工程,从明嘉靖开始,到清康熙中完成,一共三期,第一期工程,便是隆庆初完成的“新河”。
明隆庆以前,黄河多决河南、山东间曹县、单县、沛县、城武一带。徐州至张秋一段运河,时常淤塞,成为漕运的瓶颈。
嘉靖七年,为“避黄走运”,廷议南起留城,北至南阳,沿昭阳湖东丘陵边缘,另凿一条新的河道。
但开工不久,即因旱灾而停滞。嘉靖四十四年,黄河大决沛县,漫昭阳湖,运道淤塞百余里。
督理河漕尚书朱衡巡行决口,创造原运道已成陆地,而嘉靖七年所开凿的新河道“故迹尚在”,因阵势较高,未受影响,乃决定连续开挖。隆庆元年“五月己未,新河成”⑦。
“新河自留城而北,经马家桥、西柳庄、满家桥、夏镇、杨庄、朱梅、利建七闸,至南阳闸合旧河,凡百四十里有奇。”⑧(参附图一)
①隆庆元年凿成之新河示意图 (采自水利出版社《黄河水利史述要》)
这段河道当时人称“新河”,或加上地名叫“夏镇新河”、“南阳新河”,或加上人名叫“朱尚书新河”。新河凿成,是漕运一大造诣。徐阶撰《新河记》,李攀龙、王世贞、贾三近等均有诗志庆。⑨
新河既成,运道大通。安忱提到的鱼台、(徐)沛、沽头,均在旧河。隆庆元年,“移沽头主事于夏镇驻扎,管理新河一带”⑩,旧河后即渐废圮。
《金瓶梅》此处尚新旧河并提,可见写作韶光距新河之成不会太久。
万历间又悛改河夏镇(村落)南之李家港至邳州直河口,凿成二百六十里新河道,这是“脱黄”的第二期大工程,第三期工程是康熙间凿成的自骆马湖经宿迁、桃源到清河的一百八十里的中运河。
二、“南河南徙”始于何时
首先需弄清楚何谓“南河”。
与河漕有关,明人所说的“南河”,有以下数义:
第一,指从清口至瓜洲、仪征这一段江北运河。
《明史·河渠志三》:淮、扬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谓之转运河;而由瓜、仪达淮安者,又谓之“南河”。
由黄河达丰、沛,曰中河。由山东达天津,曰北河。由天津达张家湾,曰通济河。而总名曰漕河。11
由瓜仪至淮安这段运河,官方称为“南河”,民间则称为“里河”或“里运河”。
第二,指南河郎署及所统领地区。
明代为确保漕运畅通,将运河分段管治,最初大概只分南北,自丰沛以北为“北河”,以南至瓜、仪为“南河”。
后来又将清口至丰沛一段,划出为“中河”;天津以北为“通惠河”(即通济河)。
据《南河全考》,正德间,始设置总理河道大臣,“其沿河分理河务,则有工部郎中三人:北河张秋一,中河吕梁一,南河高邮一。又通惠(河)员外(郎)一人。”12
为《金瓶梅》写序的谢肇淛,万历四十一年,即以工部郎中视河张秋,著有《北河记》及《北河记余》,相称于安忱的角色。管河郎中三年一任,天子赐与敕书。安忱所言,与史合。
南河郎署原设萧县,正德元年移高邮。万历五年,划分出中河后,南河所辖区包括淮安府之清河、山阳、安东、盐城,凤阳府之泗州、盱眙,以及全体扬州府。
以是南河郎署所辖,不仅是苏北运河,还包括从清口到海口这一段黄河及从泗州到清口这一段淮河。
《淮安府志》
第三,指泗州到清口这一段淮河。
天启《淮安府志·河防》:“南河,即泗州来淮河。”13“南河”是相对“北河”说的,“北河,即今外河”14。
“外河”又是相对“里河”说的,《明史·河渠志三》:“明初运粮,自瓜、仪至淮安谓之里河,自五坝转黄河谓之外河”15。
谈迁顺治十年赴京,其《北游录·纪程》云:八月丁卯,晡后放舟渡淮河。
“淮自泗州龟山,萦回至此入于海。出泗州曰南河,宋入汴故道也。出清口曰北河。”16说得尤其明白。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东经凤阳、泗州,转东北越山阳、清河趋安东入海。
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县,自济宁、徐、邳经清河入于淮。会合口古称泗口,即后来的清口,又称清河口。泗水虽为淮河支河,古代在南北交通上却极具主要性。
《禹贡》已淮泗并称:“浮于淮泗,达于河(黄河)”;“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由于这两条河一从西南,一从西北交会于淮安郡北,所谓“淮泗环带于西北,湖海设险于东南”17,
淮扬地区居民,特殊是山阳、清河一带的居民,便合称淮、泗为“两河”,分称“南河”、“北河”。及黄河夺泗,仍此旧称。
在厘定“南河”所指之后,安忱所说“南河南徙”的“南河”,应是指从泗州至清口这一段淮河。所谓“南徙”,是指淮河原出清口东北经云梯关入海,改变为东南从运口和高堰倒灌运河和山阳及高宝诸湖。
在淮、泗安流期间,淮河是主河,而且淮泗都是净水河(故泗口称“清口”)。
但自金昌明中黄河南徙,全河夺泗入淮,夺淮入海,两河的关系便开始改变。
第一,黄河流量大,水势急,清口以下黄淮合流,黄强淮弱,黄河是主河,淮河变成支河。
第二,黄河是浊河,夹带大量泥沙,淮河自清口以下,也变成浊河。
由于黄强淮弱,淮水不能畅出清口;加以淮清黄浊,黄河的淤淀比淮河快,黄河水涨即倒注意灌输洪泽湖。造成清口和运口的淤浅。
淮水既不能从清口顺畅渗出,于是汇潴于湖。听说在弘治以前,淮河与洪泽湖还是分开的,后来连成一片,湖区迅速扩大,水面日益增高,到了万历五年,淮河终于被迫南徙。
关于此事,万历五年六月,督漕侍郎吴桂芳曾奏报朝廷:
淮水向经清河会合黄河趋海。自去秋河决崔镇,清河一带正河淤淀,淮口窒息。
于是淮弱河强,不能夺草湾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横灌山阳、高、宝之间。向来湖(洪泽)水不逾五尺,堤仅七尺,今堤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过之,此从来所未有也。18
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也有专门报告:
“
淮泗之水原从清口会黄河入口,今不下清口而下山阳,从黄浦口入海。浦口不能尽泄,浸淫渐及于高、宝邵伯诸湖,而湖堤尽没。则以淮泗本不入湖,而今入湖故也。
淮泗之入湖者,又缘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缘黄河淤淀日高,淮水不得不让河而南徙也。
盖黄水并力敌黄,胜负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废坏,而清口之内旁通济闸又开朱家等口,引淮水内灌,于是淮泗之力分,而黄河得全力制其弊,此清口以是独淤于今岁也。19
”
据《明史·五行志一》:“万历五年闰八月,徐州河淤。淮河南徙,决高邮、宝应诸湖堤。”20(参附图二)
②万历十年往后,黄淮运交汇处示意图 (采自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磋商》)
官方文书称“淮河南徙”,当地老百姓则称“南河南徙”,天启《淮安府志》云:由于“北河黄流入口”,清口淤塞,“而南河北趋之势,反却流而南。夫南河,主也;自黄河南溃,而北河始大。又使南河却流,变同趋于海之性而同注于漕渠。”
又云:“嘉靖以前,水由里河出清口而入外河,形势内高,故建新旧清江等闸,蓄高、宝诸湖净水济运。既而黄流淤垫,河身日高,水由外河进清口而入里河,故淮城、高、宝常患泛滥,而三闸反为塘水之关,是水反注而闸亦反用也。”21
这是淮河南徙的淮安版本的阐述,黄、淮则“南”“北”对称,黄运则“黑”“外”对称。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采取淮安地区的习气称呼,称“南河南徙”而不称“淮河南徙”,对我们判断书中的清河,究竟指南清河还是北清河,无疑具有主要的启迪浸染。
“南河南徙”为河运之大变。
南河承受上游诸水而无出口,洪泽湖水面日高,西浸泗州明朝祖陵,东破高堰横灌山阳、高宝,威胁百万生灵,造成极棘手的局势。
这也就难怪安忱慨叹“纵有大覃神输鬼役之才,亦无如之何矣”。当时礼科左给事中汤聘尹倡议“导淮入于(长)江”21,后潘季驯采纳高筑堤的办法,进一步提高洪泽湖水位,使南河复出清口,“淮扬免于水患者十余年”,但问题并未办理,清廷也为南河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康熙中,泗州为洪泽湖淹没。乾隆往后,黄淮益内灌,全淮由高邮湖及运河注入长江,真正完成了“南河南徙”。
“新河”的凿成和“南河南徙”,是明中叶往后河运史上的大事。
《金瓶梅词话》提到这两件事,解释词话的成书,必在嘉靖往后,其上限不能早于万历五年八月,可作定论。
这里顺便提一下,《金瓶梅》提到的凌云翼,于万历八年六月以兵部尚书总督漕运,并接潘季驯兼督河道,完成潘氏经理河工的扫尾事情。
万历十年春,开永济新河四十五里,起淮安城南窑湾,经扬家涧达武家墩,合通济闸出口;更置龙汪、永清、窑湾三闸以备清江浦之险,颇有功于漕运。
不知《金瓶梅》的作者是不是因此记住这个人,信笔写入书中。果尔,则《金瓶梅词话》成书的上限,还可移后五年,定在万历十年。
本文作者 梅节 师长西席
[注释]
①《金瓶梅词话》第1卷卷首,日今年夜安株式会社1963年版。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652。
③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页87,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吴晗《论金瓶梅的著作时期及其社会背景》,胡文彬、张庆善编《论金瓶梅》
页28、40,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⑤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34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页448。
⑥同①,第4卷,页257。
⑦谈迁《四榷》卷65,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4055。
⑧《明史·河渠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2088。
⑨于慎行编《兖州府志》卷42、7、9,齐鲁书社1985年影印万历24年刻本。⑩傅洪泽编《行水金鉴》卷265,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清淮扬官舍绣梓本。
11同⑧,页2078。
12《行水金鉴》卷165引,同⑩。131420宋祖舜、方尚祖天启七年纂修《淮安府志》,卷24,《河防·总论》,据美国国会图书馆显微胶卷。
15同⑧,页2094。
16谈迁《北游录》页24,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17同18,卷2。
18《明神宗实录》卷63,台北中心研究院史语所校刊本,1966年版,页1410、1411。
19同18,卷67,页1463。
20同⑧,页452。
22同⑦,页4317。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