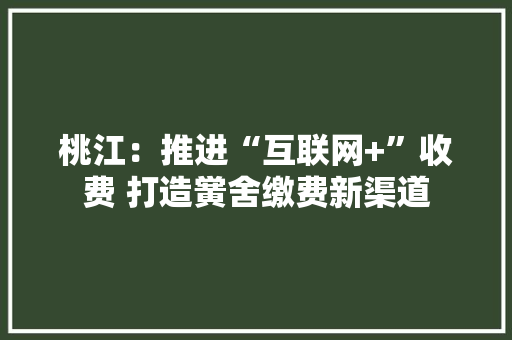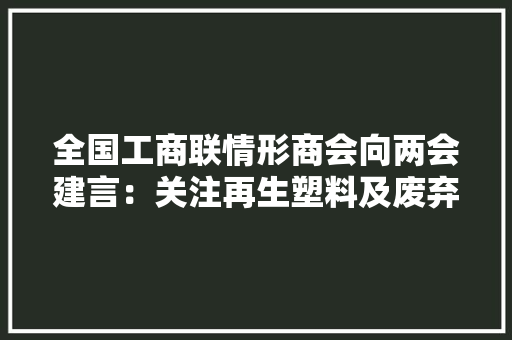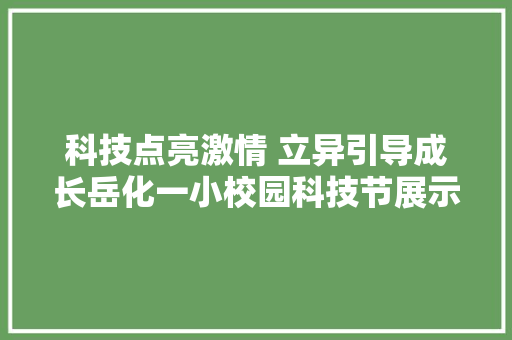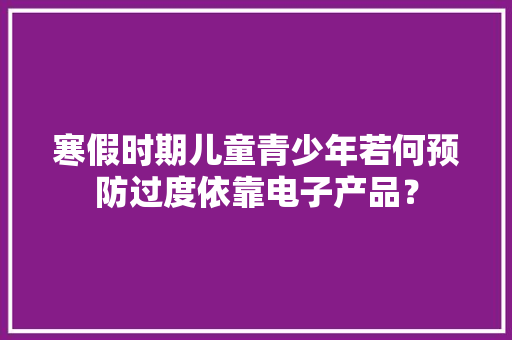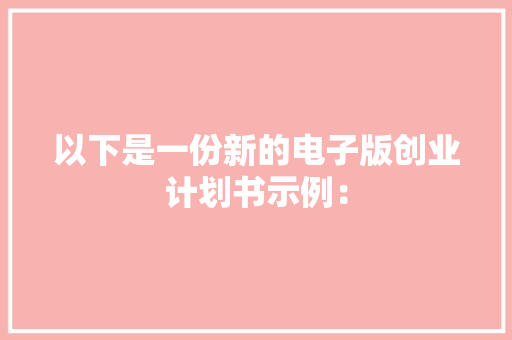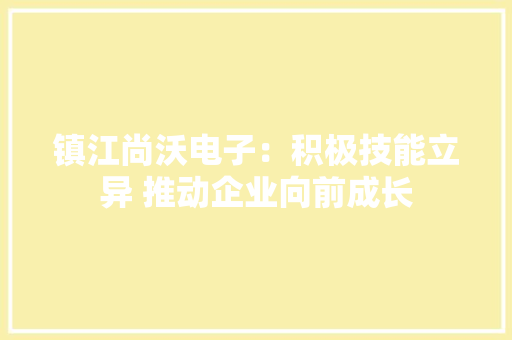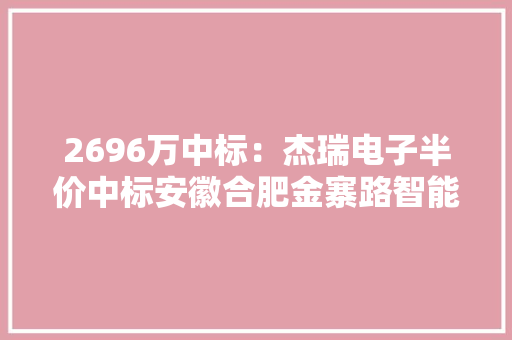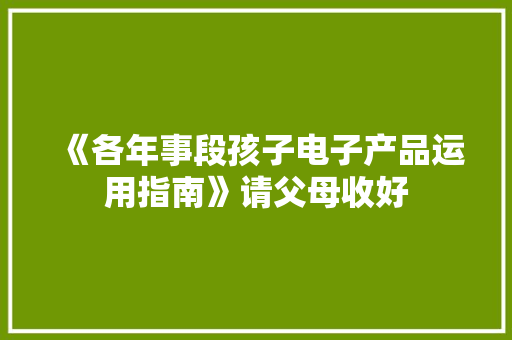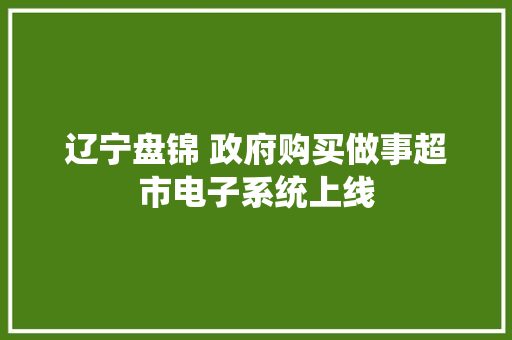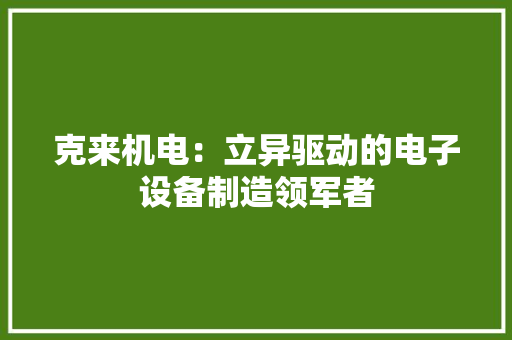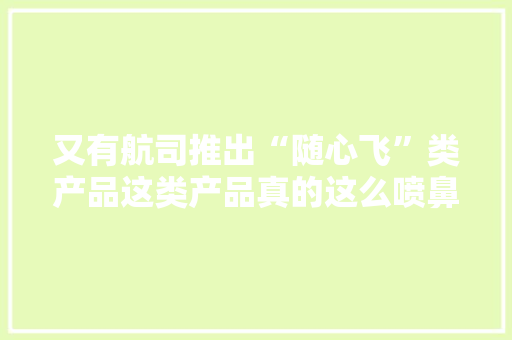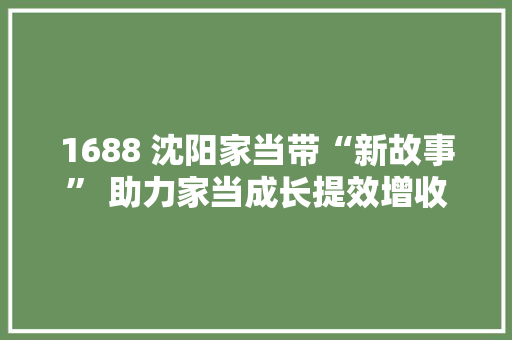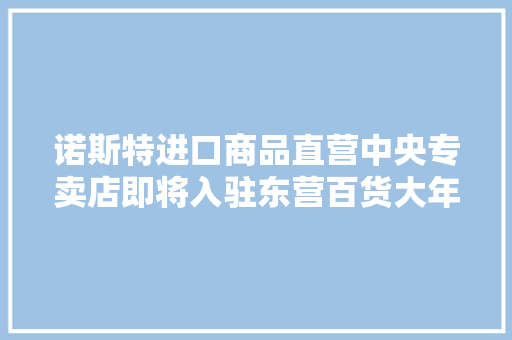发电机成为无穷尽的象征。当他逐渐适应机器排列的宏伟长廊后,开始觉得40英尺高的发电机是一种包含寓意的力量,很像早期天主教徒对十字架的觉得。与地球本身每年或逐日按部就班的传统运转办法比较,这个巨大的轮子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它以令人眩晕的速率在长度与胳膊相称的空间里旋转,仅仅发出低沉的声音,不会惊醒与电机框架间隔很近的沉睡的婴儿,只是偶尔响起能够听见的嗡嗡的警报声,见告大家它为了不流失落电能而承担了极细微的多余压力。在展览会结束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向它祷告。
将近70年之后,加利福尼亚作家琼·狄迪恩(Joan Didion)前往胡佛大坝朝圣,她的文集《白色相册》(The White Album)讲述了这段旅程。她也觉得到了发电机的心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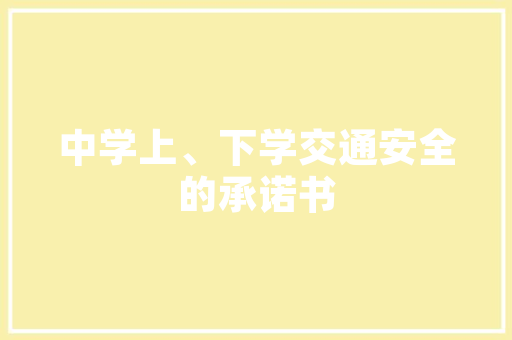
自从1967年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瞥见胡佛大坝之后,它的影像从未完备离开我的内眼。当我在某地——例如洛杉矶或纽约——与某人交谈时,这座大坝会溘然完全地浮现在脑海里,它那间隔我数百或者数千公里的保持无缺的凹面闪烁着白光,与波折不平的红石峡谷呈现的铁锈色、灰褐色和淡紫色形成比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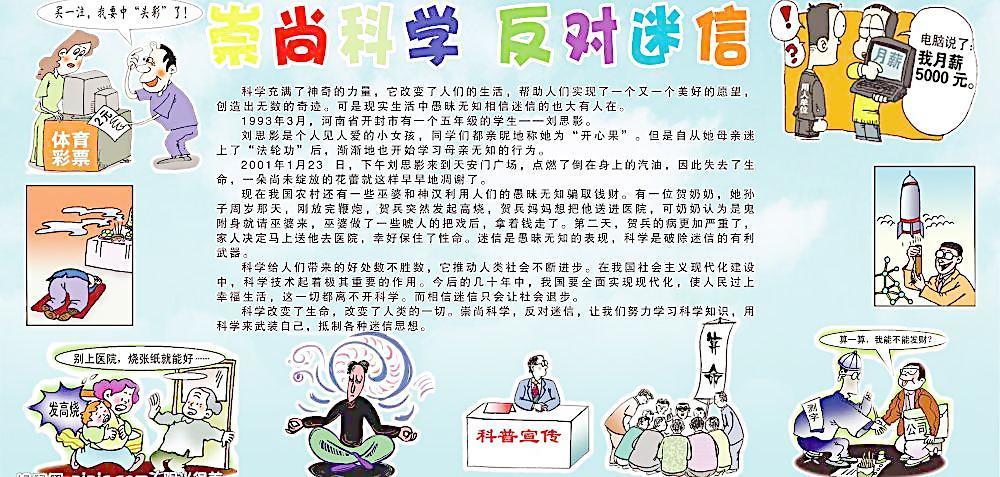
……当我重游大坝时,我与开垦局的一位仁兄一起穿过大坝。我们险些没有遇见其他人。升降台在我们头顶运动,彷佛屈服自己的意愿。发电机在轰鸣,变压器发出嗡嗡声,我们站立的铁栅在脚下颤动,100吨重的钢管向下插入水中。末了我们来到水边,从米德湖中抽出的水咆哮着分别流过30英尺高的水闸、13英尺高的水闸,终极进入涡轮机组。“摸摸它”,开垦局的人说,我照着做了,很永劫光我就站立不动,手放在涡轮机上。这是奇妙的时候,统统含义尽显无遗。
……我穿过大理石铺成的星座图,开垦局的人见告我,这张图绘出了两侧昼夜平分点的转轴,而且永久不变,随时等待所有能够看懂星座图和大坝落成日期的人。他说,这张星座图预示了何时人类都将消逝而大坝将保留下来。在他先容的时候我没有细细琢磨,但过了一下子,我开始品味他的话语,此时风儿哀鸣,太阳落至山后,只留下一抹余晖悬于半空。以上无疑便是我常常想到的景象,但我未能深刻认识到个中的意义:发电机终极将分开人的掌握,完备与世隔离,在这样的状态下铸就它的辉煌——向无人存在的天下输水输电。
当然,大坝不仅引起敬畏和讴歌,而且让民气生恐怖和反感。高耸的大坝使目标武断的鲑鱼和其他产卵鱼类的洄游受阻,而且造成大水淹没家园。在技能元素领域,厌恶和敬畏常常结伴而行。我们对待最大的科技创造物,就像对待让我们既反感又敬畏的人一样,它们激起了我们最深切的爱与恨。另一方面,没有人曾经被红杉搭建的教堂厌恶过。在现实中,没有大坝——纵然是胡佛大坝——将永久矗立在星空下,由于河流有自己的欲望,它们在大坝的楔形面后面堆积泥沙,这样河水终极将漫过大坝。可是在这个人类劳动的结晶耸立的时候,它赢得了我们的敬畏。我们可能认为发电机将永久迁徙改变,就像我们觉得自己的心脏必定永久跳动一样。
对人造品的激情亲切涉及面广泛。险些每一件人类制造的事物都有崇拜者。汽车、枪、饼干桶、钓竿卷盘、餐具,随便举例。时钟“令人惊奇的精密度、勤奋和实用性”得到一些人的喜好。对另一些人来说,吊桥或者像SR71和V2这样的高速翱翔器所具有的美感是人造品的最高峰。
我们具有技能崇拜的生理,即一种对科技的迷恋。人类借助自己创造的工具实现从智人向当代智人的转变,就本性而言,人类天生就有创造物品的喜好,部分缘故原由是我们本身便是被创造出来的。另一部分缘故原由是:每一种技能都是我们的孩子,以是我们热爱所有的孩子们。我们热爱科技,至少有时候如此。承认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尴尬。这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