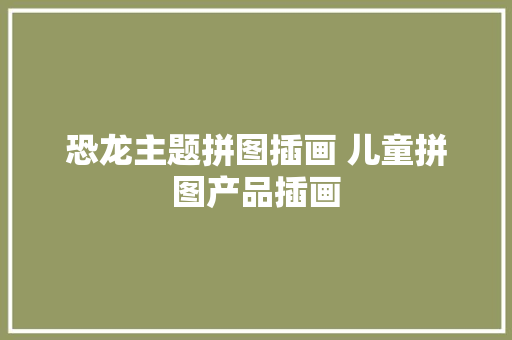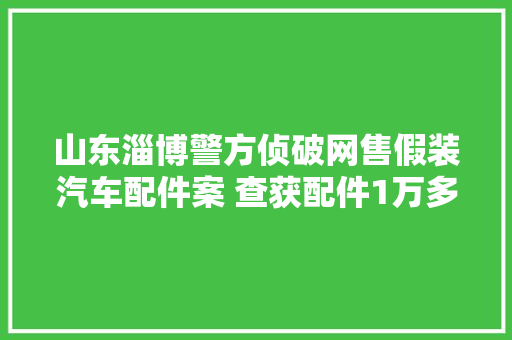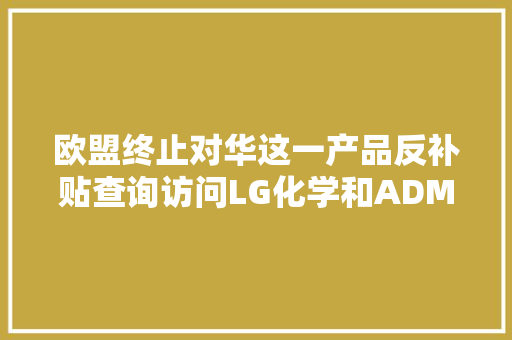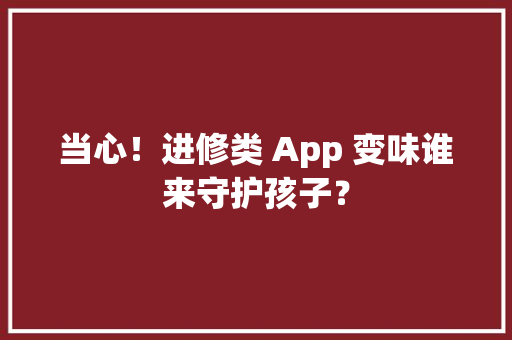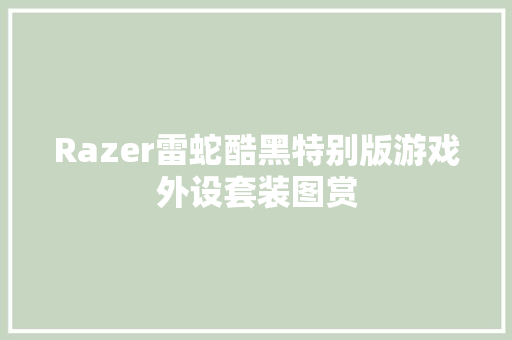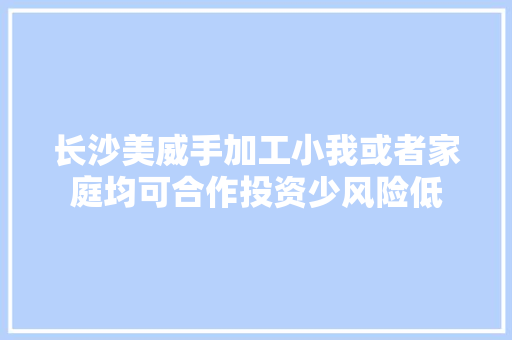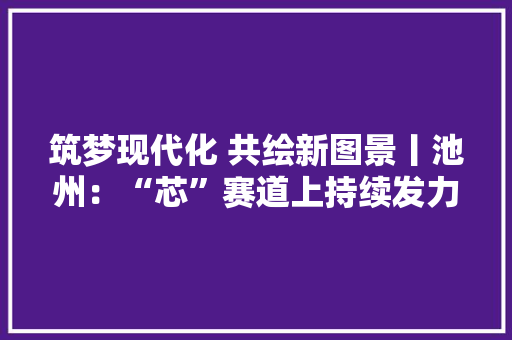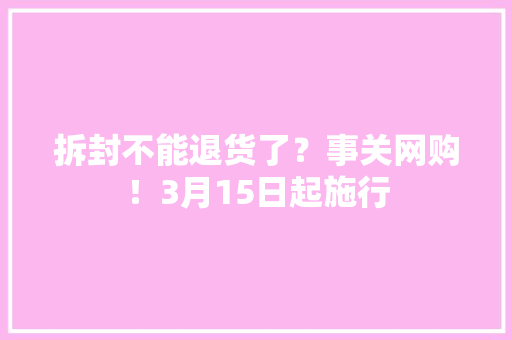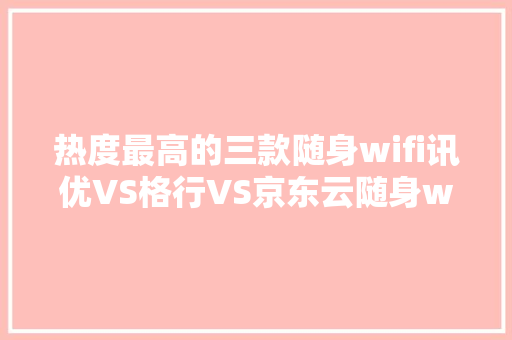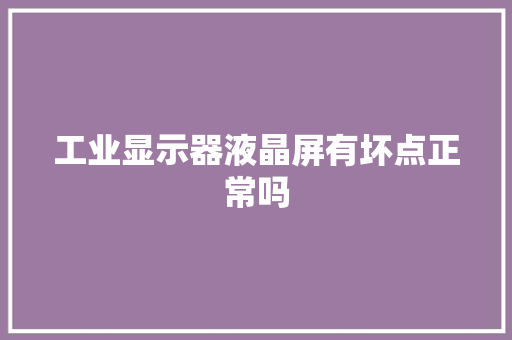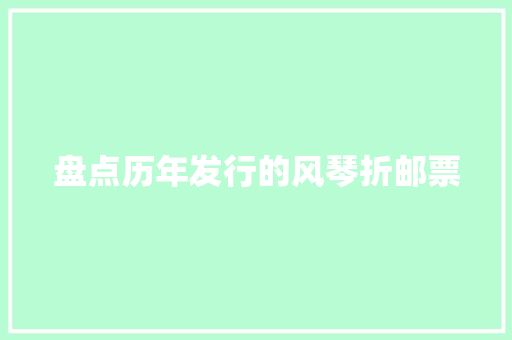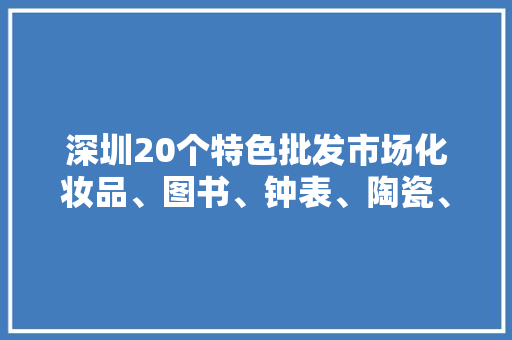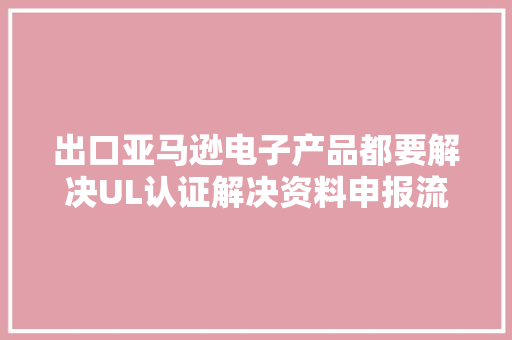《诗刊》2019年第8期推举
彭志强,1977 年生于四川南充,现居成都
挖 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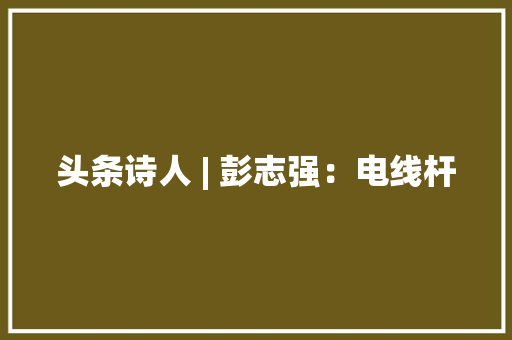
天还没亮,一条长长的电线

像沉睡的蛇
蜷缩在山腰
驻扎在培植营地的他习气了
跑步提高,赶在灯光点亮千家万户之前
完成他的黎明
这次的任务不是从流水里取出隐秘的闪电
而是给三十根实在的电线杆寻觅
安顿青春的寓所
当一盏灯敦促一个人成为光源
当一座山敦促一个人成为靠山
手中的军用铁锹便分不出性别
泥土红了。挖洞和生娃一样,得早
到了须发与洞口齐平,人如一口深井
天亮的时候,内心和杆洞才更敞亮
他摆荡的铁锹很永劫光都没有停下来
只因贵州山区新增那条22万伏高压线
早就喊破了嗓子
抬 杆
上山。一曲电工号子
一样平常是八人合唱:哎嗬—哎嗬—哎嗬……
负重前行,腿不能抖,激情饱胀的汗水
才会精准指引电线杆放于山腰或者山巅
顺着洞口插入电线杆,仰望天空
让它笔直,俯瞰村落与城镇
烈日又一次败给父亲
和他的工友们劈面扑来的两袖清风
此刻,他们挺直腰杆给电线杆敬礼
一排排电线杆停下来
站得整整洁齐,也给他们敬礼
向脱下军装依旧是军人的电工们敬军礼
“你看,你看——
滚滚烈日滚下了山……
电线杆学会站军姿,
便是长城耸立不倒!
”
多年之后,退休的父亲
每次和电线杆狭路相逢,还会敬礼
不仅是致敬深山线路培植那段日子
还由于电线杆是他生平不变的军姿
拉 线
把电线拉直,或许比把风拉直还难
由于电线不像风可以随意拉直自己
得靠电工左手把着电线杆,右手紧握电线
踩着脚踏板一步一步攀爬
一欠妥心踏空,便是热滚滚的汗珠
坠入电线的峭壁
最难的是在瓷瓶上穿针引线
假如白云飘过,还得把电线穿过云的瞳孔
铝线还好。举过肩头就能缠紧瓷瓶
让蓝天和雨天平衡于平行线
铜线显得很倔强
它不太听人使唤
父亲要带领两拨人在两座山头拉线
形同拔河,才掌握住铜的叛逆与线的反弹
安装高压线的人便是这样
永劫光和电线相处,他们的体内早已血虚
一旦灯呼唤光,电视呼唤电流
他们又满血复活,送电,给贫穷的山水***
只管放出的电线已可环抱无数圈祖国的边陲
他们却常常紧捂家中开关,不让电虚耗一度
修 塔
火线碰零线有时不亚于喝醉的汽车相撞
塔,便是以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坍塌
不是传说中堆砌的雷峰塔
是曾经耸立在峭壁边的电力铁塔
他们用一个多月的毅力铸就的塔
在电视里轰然倒塌,像人溘然瘫痪倒地
这原来是雷的不是,或者雨的多事
应发明更暴躁的雷劈去世那可恶的雷
可是熄灭的万家灯火无法体谅
闪电的命令,还是把他们再次推上峭壁
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抢修塔
犹如给漏洞百出的空牙床补牙
没错,梯子一贯在岩石的脆响里打滑
没错,被雷雨冲散的铁都还给了泥土
抢险的集结号一吹响,那便是打仗
总得有人在雷雨中逆行,匍匐提高
他们没韶光做进与退的选择题
只能把危险扔之脑后,把信念紧握手中
父亲平常放在床边的军用胶靴
这一夜,与雨水一起彻底失落眠
跳 闸
夜才真的漆黑。
变压器,被南明河边几个居民小区的人
骂成一坨废铁。鼓噪就快止不住——
电锅怎能没有电养活
冰箱怎能没有电补给
空调怎能没有电调和
夜饭怎能没有电燃烧的灯泡陪伴
……越来越多的抱怨声
包围了无辜的变压器
以及变压器旁伶仃无援的电线杆
实在是过度透支的电
让电线吱吱吱地退却撤退
心明眼亮的父亲和工友们一边说
一边背上电工箱,连忙提高——
“不是大略地短路断开了断路器,
而是酷热的鬼景象吸走太多的电!
”
居民一脸茫然,显然听不懂
他们跟电线互换的措辞
必须抢修线路,换掉烧坏的电线
疏通堵在10千伏变压器心脏的心病
电线、电笔、电工刀、电动夹钳
开始了专一苦干……
经由改动的电流,才成功阻击了夏天
这只烧得通红的猛兽
此刻,漆黑的南明河
和祖国一样灯火通明
先前骂爹骂娘的人,都已悄悄静回家
线路年夜夫
自从50万伏电流穿过他的身体之后
这个幸运活着的电力外线工
又多了一个身份:线路年夜夫
实在是他和水泥电线杆一同朽迈了
无力再攀爬上去眺望
隔着电源千山万水的水电站
父亲索性转移战线
从外线工到内线工
掩护变压器以及变压器一带街邻的安危
手里的工具变换为
电笔、胶布、电工刀、电工钳
以及连接室内电器的插座、绝缘体电线
没曾想这样的内线工越老越吃喷鼻香
许多时候仅用一支电笔
就能点破老插座和旧灯泡的顽疾
纵然是电视机的线路营养不良
或者砖墙里电流不畅等新毛病
他也好手到病除
70岁的人了,一听邻居喊一声老彭
“快来帮我看看电表怎么瘫痪了”
他哪里像个弱不禁风的老者
分明是心急火燎的线路年夜夫
锐 评
正 方
电线杆上的父亲以及中国的脊梁
马知遥
这组诗歌来自四川墨客彭志强,由六首短诗组成,读完后,整体诗歌的饱满和感情深深打动了我。这不仅是一组描写现实劳动场面的诗歌,有着中国传统咏物诗的特点,借助自然万物咏叹生命的壮丽和心灵的颤动,讴歌劳动本身的美;更是在写一个大时期中不断奉献、甘于奉献的父亲,一批有同样奉献精神的时期模范,他们来自基层来自平凡人家,但绝不平凡。
写实题材的诗歌创作是有难度的,难在“实”,由于描写的工具便是现实便是事情场景,或者生活中的榜样,而且须要直面讴歌,这与诗歌作为艺术创作表示的“虚”形成了反差,文学的想象力面对现实时,有时是无语的,乃至是无力的。这时磨练墨客的紧张不在于诗歌的技巧而在于文学的素养。即他是否有能力把现实之实加入想象,加入必要的诗意,既能传达现实又能通报美好。墨客彭志强在他的作品中做到了。比如他的诗歌《挖洞》。本来呆板的劳动场面,经他诗歌的传达一下子有了活气。一大早就起来赶到工地挖洞,为直立起三十根高压线,军用铁锹一刻一直——由于贵州山区公民用电的须要。本诗彷佛便是要解释这样一个朴素无华的事实,但转化为诗歌的时候,墨客把竖电线杆叫做“给三十根实在的电线杆寻觅 /安顿青春的寓所”,而挖坑的紧迫感和必要性,他用诗歌表达为“当一盏灯敦促一个人成为光源 / 当一座山敦促一个人成为靠山 / 手中的军用铁锹便分不出性别”,为了公民的须要,为了贫苦山区对电源的须要,他们自己成为光源,他们自己成为靠山,他们乃至在劳动中已经不分男女,昼夜兼行。
整体上,这组诗歌把一个电工的生平或者他紧张从事的项目都逐一列出。这些看似白描的表达,潜移默化中有了冲动民气的力量。比如《抬杆》这里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描写父亲和工友们头顶烈日抬电线杆上山,然后立起来,在烈日下专一苦干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却也在暗示着父亲曾经是一个军人,革命军队的优秀作风让他更加努力和坚毅。当看到立起的电线杆,仰望劳动的成果时,墨客写道:“此刻,他们挺直腰杆给电线杆敬礼 / 一排排电线杆停下来/站得整整洁齐,也给他们敬礼/向脱下军装依旧是军人的电工们敬军礼”而这样的精神状态一贯延续到父亲退休之后,每当看到自己亲手直立的电线杆,他还会敬礼,那里透着的是一个父亲对职业的尊重,是一个老父亲对过去岁月的珍惜。看似劳苦的最基层的事情,在一个父亲那里已经是一辈子最宝贵的光阴。
在诗歌《拉线》里,我们仍旧能看到对电工细致的事情场面的再现,那便是现实便是实情,墨客的笔在那一刻显得如此深情。这让我想到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主要一维:情绪的温度。抒怀诗歌尤其如此,苍白的大词抒怀和单线直抒的表达办法险些让当代诗歌的抒怀近乎血虚,但在彭志强这里,没有造作,多的是对生活细节不雅观察后的真实感想熏染以及笔墨带出的深情。墨客描述了不同材质的电线在安装过程中的特点和难度,刻画了父亲事情的困难,更凸显的是一线电工的艰巨事情,在表达电工们艰巨奋战无私奉献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一些现实主义题材诗歌的标语口号,有的是细节的展示,其态度在细节中呈现而且张力十足。在诗歌《修塔》一诗中,墨客这样写道:“火线碰零线有时不亚于喝醉的汽车相撞 / 塔,便是以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坍塌”。该诗复原了电工们修复“电力铁塔”的过程。先是电力事件导致铁塔的崩塌,然后用诗意的办法表述了雷电的缘故原由导致电路短路铁塔涌现问题,同时也表达了断电给居民带来的困扰,在不理解和焦虑中,在雷电的景象里,电工被推上“峭壁”,他们既要攀登位于高处的峭壁修复铁塔,同时也要面临死活的“峭壁”去冒险。别无退路,为了让电力规复。“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抢修塔 / 犹如给漏洞百出的空牙床补牙”多么贴切的比喻,既表现出抢修事情的难度,又将雷击之后电力铁塔遭损的惨状呈现。透过征象动用文学的想象力,逼走平庸的现实,又呈现现实的残酷,诗歌的当代表现力,新期间诗歌的表现力当如此。
诗歌《跳闸》更是把一个常见的社区场面呈现到读者面前,黑夜中断电跳闸,而且是一直地跳闸,这引发的小区骚动是一定的。是的,没有电带来诸多的问题,生活是最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少了电就无法正常运转的时期,人们在享受电子产品的同时也成为电的俘虏。这里墨客没有进行理性的当代批驳,由于那不是诗歌的功能,他更多的是用文学的想象力和描述能力表达着变压器破坏后的事宜本身,以及个中的诗意。熟习的场面,在酷热的夏天里,最劳碌的是要让鼓噪和骚动平息的电工们,父亲和他的同行在和夏天作战,在最困难的时候让通畅的电流办理问题。以是墨客这样写道:“经由改动的电流,才成功阻击了夏天/这只烧得通红的猛兽//此刻,漆黑的南明河 / 和祖国一样灯火通明 / 先前骂爹骂娘的人,都已悄悄静回家”我们常常批评当代墨客们阔别了当代生活的现场,阔别了普通人的生活,在大量复制的私情中泛滥感情,我们乃至疑惑当代墨客失落去面对生活现场的书写能力。但彭志强的诗歌彷佛在强调,只要你还具有墨客的情怀和任务,你就可以直面现实最熟习最真切的部分,把那些看似无法进入诗歌的部分写进诗意,写进读者的不雅观察和情绪深处。电工,父亲,还有看似朴素无华的人和事,在一系列的小情节小场面里,我们看到了阔达的情绪、翻滚的激情和才华四溢的对生活的诗意传达。我的父亲是电工,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的父亲生平都奔波在掩护电力的途中,彷佛墨客一贯在这样说,但对父亲的理解和爱,没有用一个字直白地表达,我们却能真切感想熏染到墨客对父亲的深奥深厚的爱,对电力事情者的理解和关怀。
这组诗歌与其说是讴歌电工、讴歌时期,与其说是给父亲的一组赞颂诗,不如说它更是对新时期诗歌创作方向和功能的大胆宣示:我们的墨客是可以直接拥抱时期,是可以直接抒写和拥抱创业者的,并不是只有描写个人心灵和灵魂苦难的诗歌才是诗歌,诗歌还有她另一个功能,便是对时期真切的关注,对普通人和他们身上表示的时期精神的挖掘和讴歌。如此,诗歌的功能才能多元,诗歌的功能才不会阔别生活和百姓的视野。
反 方诗有法,意有度
冯 雷
从题材的角度来讲,《电线杆》所反响的电力工人、电工师傅辛劳劳作的场景的确让人以为面前一亮,由于它有别于时下常见的对心灵迷宫的不雅观光游览,和之前“底层”的凄冷、暗淡也不太一样,它显得更加外向,更加富有生活现场、事情现场的力度与质感,更加言之有物,就态度和意义而言还让人遥遥想起前些年终于“公民性”的谈论。以是无论是做正方还是反方,这一题材都值得肯定。诗歌可以兴、可以不雅观、可以群、可以怨,但所有的统统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作诗的办法方法上来。而正是在办法方法上,《电线杆》却不那么令人满意。
《电线杆》里最能干的不敷莫过于有些表达过于“散文化”乃至是“作文化”。“五四”以来诗歌最常见的一个毛病便是“连而为文,分而为诗”,行文连贯、粘滞,缺少跳跃。令人遗憾的是,《电线杆》偏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挖洞》的前六行里,“完成他的黎明”还有一定的陌生化效果,谓语“完成”和宾语“黎明”之间属于非常规组合,但前五行“天还没亮……驻扎在培植营地的他 / 习气了跑步提高”,这样的表达是不是显得太平铺直叙、顺流而下,太“连而为文,分而为诗”了?《线路年夜夫》的第一节也是同样的问题,三行诗连起来,自从五十万伏电流穿过他的身体之后,这个幸运活着的电力外线工又多了一个身份:线路年夜夫”,这显然是一个完备合乎语法规范的句子。比较之下《抬杆》和《拉线》的第一节才更像是诗歌的表达。比如《抬杆》,按照正常的语法语序第一句该当是“上山(时),一样平常是八人合唱 / 一曲电工号子”,而作品里却做了一点颠倒、调度,虽然限于篇幅尚未显现出多少精彩之处,但至少不同于散文的写法。在我看来,《挖洞》所暴露的问题不但是表达上的瑕疵,更在于行文思维上的散文化。还是看《挖洞》的前两节,墨客先交代韶光“天还没亮”,再铺陈环境“电线 / 像沉睡的蛇 / 蜷缩在山腰”,然后是主人公登场“驻扎在培植营地的他习气了 / 跑步提高”,韶光、地点、人物,包括氛围一样不缺,这种完全、严密的交代是不是更像是叙事性的文体?再往下看,“这次的任务”“不是……而是……”,“当”若何若何,“便”如何如何,这种主谓宾式的语序、这些表达特定逻辑关系的关联词语使得句子的表情达意变得非常“精密”,但是这种“精密”恐怕并不是诗歌追求的。在 20 世纪初,美国的“意象派”墨客便对自身所持措辞的“精密”感到不满,而对汉语入诗时的表现力大加讴歌,在他们看来,汉语语法灵巧自若,完备可以摆脱线性逻辑关系的限定。新文学早期“要须作诗如作文”的口语诗实际上走的也正是“以文为诗”的偏锋。因此《电线杆》里“散文化”的问题不但是某一次、某一首的有时失落误,实际上表示的是墨客“文法”不雅观念过剩、“诗法”意识不敷的不雅观念问题、认识问题。比如看《线路年夜夫》,第一节里,“自从”如何如何,主人公“又”若何若何,这种前因后果式的、线性的思路,读起来是不是更像是一个小说的开头?接下来的几节里,“索性”“没想到”“纵然”“哪里……分明”,这些没有实际意义、只卖力逻辑顺序、关系的副词极其逼迫地规定了阅读的路线,没有旁逸斜出,也不许可含混和朦胧,只有“高大上”的主人公,这彷佛更靠近***稿的阐述办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像《挖洞》《线路年夜夫》,虽然有的句子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但整体上看从外到里都太过于“散文化”。
正如前面所肯定的,《电线杆》在题材上比较讨巧,但是福祸相依,作者对前辈人物的塑造有时却不免陷于某种程式化的“腔调”之中,比如《修塔》里的“只能把危险扔之脑后,把信念紧握手中”,带有浓厚的革命话语气质。再者如《跳闸》的第二节,且不说“夜饭”是否是披了“晚饭”或是“夜宵”的蹩脚马甲,也暂不深究“电饭锅”是不是为了和“冰箱”“空调”“夜饭”保持同等而硬是从三字词瘦身成了二字词,包括“电”和“养活”“补给”“调和”“燃烧”的主谓搭配是否妥当也先放一放,我当然可以理解墨客意在通过四行“怎能”来表现跳闸后小区里怨声四起,但是这种主不雅观想象是 否略失落浮泛和公式化呢?
选自《诗刊》2019年第8期
敬 请 关 注
中国诗歌网
诗歌报刊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