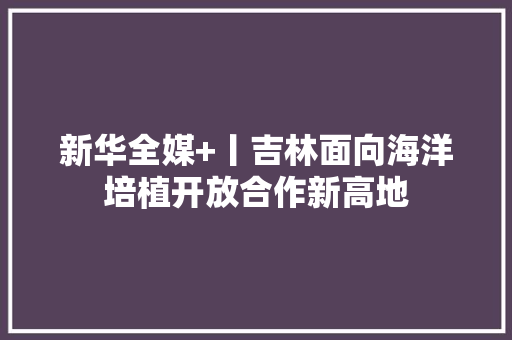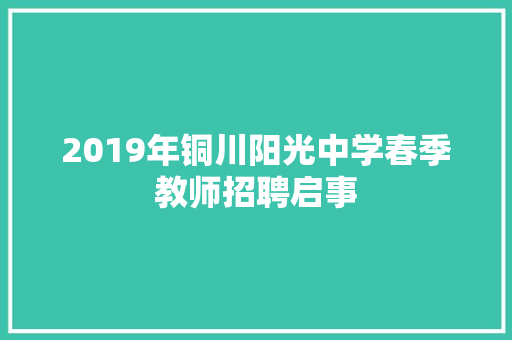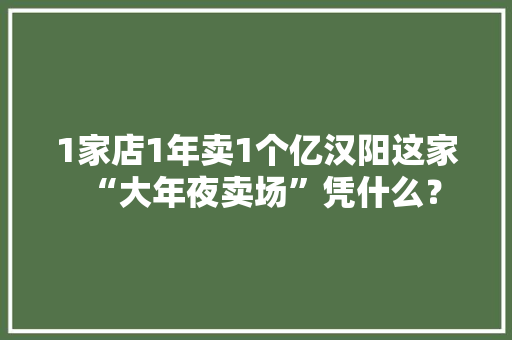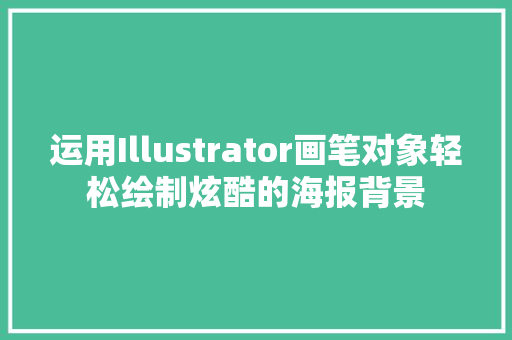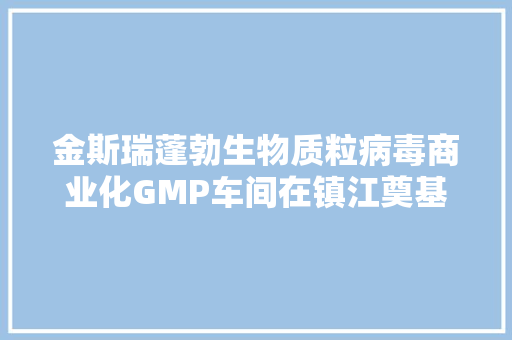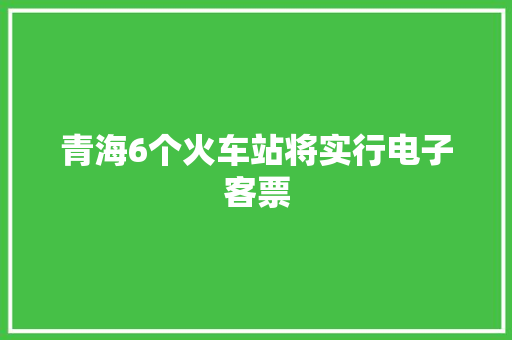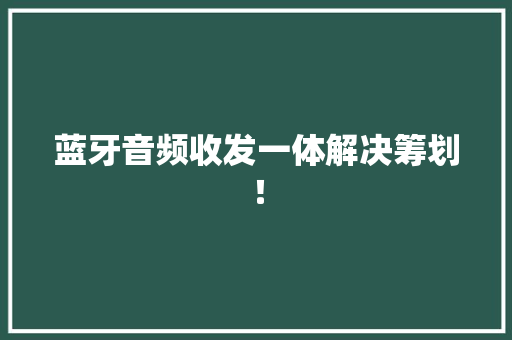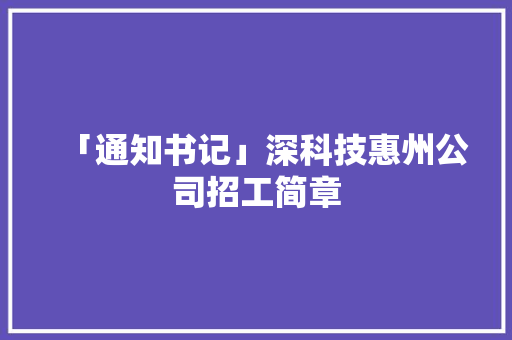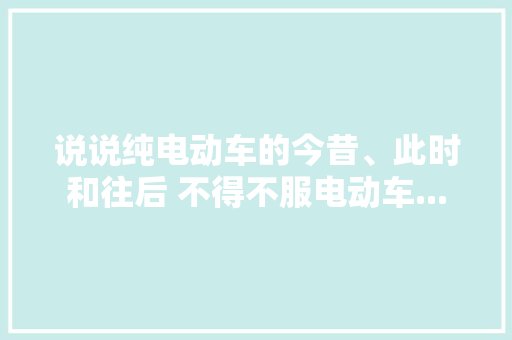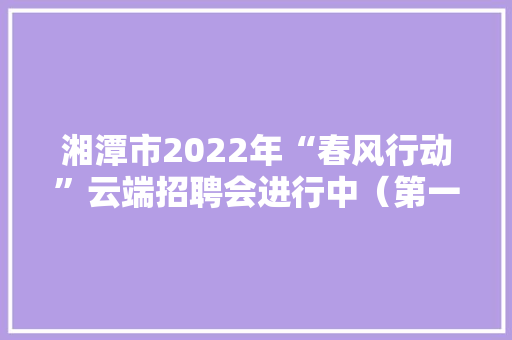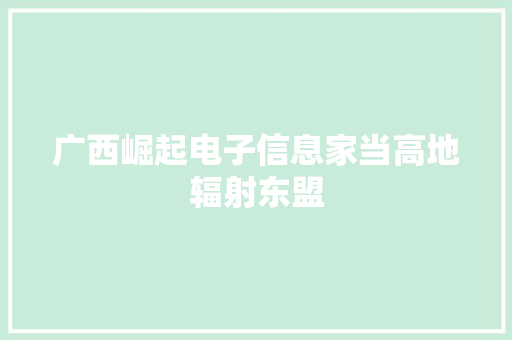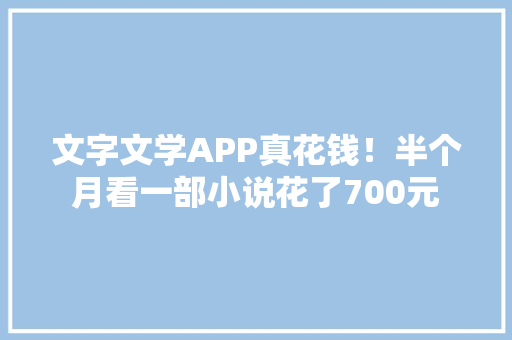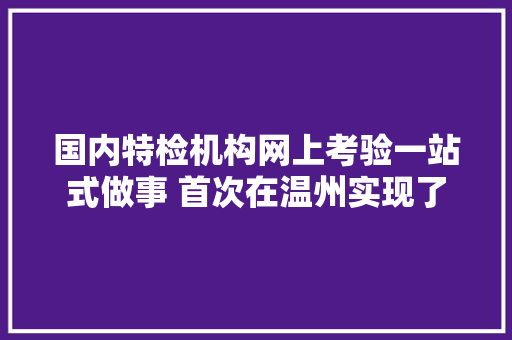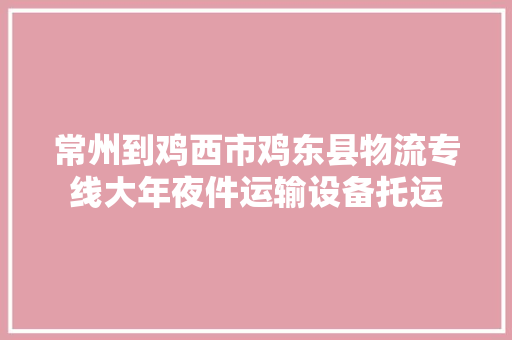这个七月,中国传媒大学范小青老师荣获韩国文化家当振兴院的奖励,表彰她对中韩文化互换作出的贡献。与此同时,她的新著《韩国电影100年》出版,作为第一部系统讲述韩国电影百年史的威信书本,由中国学者率先写作完成,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
中国著名导演王小帅夸奖范小青为有兴趣理解韩国电影及社会的人“梳理出一条专业的路径”。釜山电影节前理事长李庸不雅观评价道,“20多年来,范小青亲历了韩国电影的飞跃式发展,踏踏实实研究,以外国学者的视角回顾韩国电影的100年历史,对韩国电影而言弥足宝贵。”韩国著名导演李沧东说,希望这本书能让韩国电影爱好者对韩国电影的历史不再局限于碎片式的走马不雅观花,同时生发对“电影是什么”这一实质问题的关注,共同思考电影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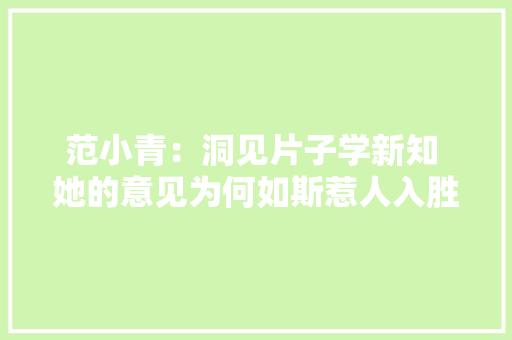
8月6日上午,范小青获奖后接管北京青年报的独家访谈,讲述她写作这部书的背景渊源,并分享了她对中韩文化互换的切实体会。范小青声音明丽,语速较快,温和中不失落锐利,令人感想熏染到“她力量”通报的聪慧与能量。“我喜好跟影迷互换,希望更多的读者看到它,引发对电影文化的思考。”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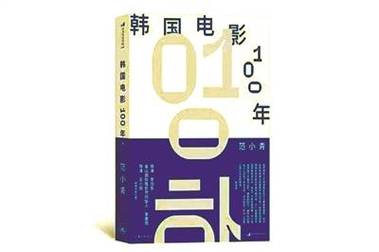
2000年被《绿洲》《春逝》打动,辞职去读电影学
北青报:您是如何开始对韩国电影产生浓厚兴趣的?
范小青: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给几家北京的报纸写影评文章,也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一起去看电影,那时候大家看的大多是东欧、好莱坞,包括日本的电影,我当时很少听过有韩国电影的声音。当我2000年第一次看到李沧东导演的《绿洲》和许秦豪导演的《春逝》,就被影片深深打动。后来在北京电影学院看韩国电影展,感想熏染到韩国电影在类型上是好莱坞式的,但是它的情绪表现是东亚式的,非常细腻,跟我们更加靠近,更能引发我们的共感。这种电影当时我没见过,就开始关注韩国电影。但那时候韩国电影还没有大火,在世界范围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认可。只是2002年韩国导演林权泽凭借《醉画仙》得到第55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同年李沧东导演的《绿洲》拿下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以及新人演员奖。
当时我在电台事情,作为主持人常常采访一些文化圈的名人,一次闲谈天,韩国导演金泰均有时问我,你想不想去国外读书,去学电影?我就正式想了想这件事,开始为留学做准备。后来他特殊热心地帮我联系导师,乃至给我做包管人。给我觉得无论是他们的电影,还是电影人,都很诚挚,知行合一。2003年,我从北京交通广播电台辞职去韩国读书。
北青报:作为第一批去韩国读电影学的留学生,您有哪些难忘的求学经历?
范小青:我特殊幸运的是,当时海内还没有太多年轻人去韩国学习电影,而且我学习的过程恰好经历了韩国电影暗自发力到全面着花的过程,相称于是在历史当中感触到韩国电影的历史。
我在中心大学读书时,我们班就我一个中国留学生,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们那拨儿老师都特殊棒,教授中还有两位电影导演、一位著名拍照师。中心大学电影学专业的授课不仅仅是在教室里完成的,当时有一位教授李圣求是韩国最老的教授之一,他带我们上韩国电影史,我们学校离韩国电影资料院很近,坐三四站地铁就到了。每个星期我们上课的时候,他都会提前联系好电影资料院看什么电影,然后免费给我们这个班的学生放电影,放的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白电影,还有没修复好的中间声音丧失落的那种老电影。看完电影我们再回到教室用学术的办法谈论。全体四年的学习过程中,老师讲授的很少,紧张便是师生之间的沟通、谈论。
不仅在大学教室积累知识,还和韩国电影文化圈有亲密互换
北青报:这样的求学经历,也成为匆匆使您撰写《韩国电影100年》这样一部讲述韩国电影历史著作的契机吧?
范小青:是的。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韩国电影当代化的家当进程》,也启示了我后面的持续研究。《韩国电影100年》是我学习、研究韩国电影20年交出的一份作业,也是很多对韩国电影的“现在”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和影迷们一贯津津乐道的“韩国电影为什么会有本日的造诣”这个问题的一个剖析与总结。但是在写这本书时,我自己是影迷出身,又写影评,我并不想写一个生硬的学术著作,以是我力争用盛行文化的阐述,把韩国电影分为四老天王、四大天王、四小天王、四大天后等跟影迷互换,这个过程特殊有趣。
事实上,我对付韩国电影的感知还有主要的一点,便是有一种电影文化的沉浸感知。韩国电影文化机构的候选人全都是来自教授、和现场事情职员,比如我们的老师都是各个电影文化机构的大人物,像李忠植教授是电影振兴委员会的第二任委员长,朱贞淑教授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女学者,她曾经做过韩国电影资料院院长。
我印象很深,每当举办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时候,首尔有名的电影高校都会放两周假,教授和学生们都去釜山看电影,而且前辈们会很早就抢订两个公寓,我们女生都住在那里。电影节期间还会给电影专业的学生提前申请一张免费影迷卡,凭影迷卡每人每天可以拿到4张免费票,上午10点看一场,中午1点看一场,下午3点看一场,晚上6点看一场。看完这几场电影,老师们会把我们一拨一拨都带上,跟资深电影人一起用饭,谈论电影。全体电影节期间我们都是沉浸在电影文化的氛围当中。
北青报:您留学读书的过程都很顺畅,还能够深入到电影艺术的各个方位。
范小青:我自己是主持人出身,对陌生环境以及与人互换这方面,首先我不怵,其次由于我非常努力,措辞进步得也非常快。其余,我的电影文化积累并不仅仅是在中心大学的教室里进行的,我和韩国电影的主创职员、韩国的文化圈有非常亲密的互换,每周有三四场我都会去到电影发布会现场。
这种互换缘于2004年,一开始金基德因《撒玛利亚女孩》和《空房间》连续捧起柏林和威尼斯两个最佳导演奖。5月,朴赞郁又凭借《老男孩》得到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由此,韩国电影开始引发环球关注。但是当时在韩国电影圈会韩语的中国人不多,险些没有人能进入他们的语境里一探究竟。刚好我做过,又写影评,以是很快《看电影》杂志就找到我承担一些采访宣布。那时我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电子邮件,从韩国电影导演到明星,以及幕后的事情职员。每次在电影互换的文化现场和韩国主创们对话,每人站起来都先自报家门,我险些都是唯一一个华语圈的。大概从2005年开始,喷鼻香港有线电视台约请我做制作人、出镜,以是我跟韩国电影圈的大主创们也有了更多的互换机会,对韩国的大众文化更多了直不雅观理解。
北青报:能够一贯保持着愉快状态,以前的职业历练对您也有所助益吧。
范小青:对的。我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不管是在学校学习人文社科的方法论还是后来的事情履历,到现场采访、写评论、做节目,都蛮有用的。每当我在电影发布会现场举起手提问,他们就会创造,这还有一个中国。这对付他们来说是有一定的印象,也有利于我后续的事情。比如李俊益导演拍《王的男人》期间,可能我在现场的互换给他留下的印象比较深,所往后来我再约独家访谈就比较顺利,而且我想要补充什么内容,他都会努力去帮我完成。
采访近30位韩国重量级电影人,他们大都诚挚、率直
北青报:您历时3年,采访了近30位韩国电影界重量级人物,在《韩国电影100年》中,这些翔实的口述佐证了历史。李沧东直言,在韩国电影界,如果没有深厚的相信和交情为根本,这样的口述实录调研很难实现。您在与韩国电影人交往中有哪些印象比较深的事?
范小青:总体来说,我打仗到的韩国电影人大都比较诚挚、率直,大都生活非常简朴。他们没有那么繁芜的程序性或者是身份感,做什么事情都有板有眼,让我以为特殊踏实。比如约采访都是说好一个地方,我们坐地铁去,然后喝一杯咖啡就开始聊。如果我还想知道一些家当方面的信息,他们乃至会把PD(制片)带上,我们一起聊。
有件事比较触动我,当时美国一个大投资集团有个拍片操持,想拍一个秦始皇东渡日本的奇幻片,于是想要找一个善于拍古装片的韩国导演,当时古装电影《王的男人》火遍亚洲,我就推举了李俊益导演,对方也以为特殊得当,请我翻译剧本然后去跟李导推进这件事。但李导对此事迟迟未回。有一次我追问他,他说他看了剧本,投资很大。我说,是的,投资很大。末了,他说他正在准备一部电影,实在抽不出韶光,他还说中国不缺这样的导演。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时正在准备的电影是一个叫做《东柱》的黑白片,讲一个在韩国尽人皆知的国民墨客尹东柱的故事,投资一共200万公民币。我就想,如果当时他接了那个大项目,他个人的酬劳都该当是这个电影制作费的三倍,那么大赚特赚的项目他为什么不接?李俊益导演说,“我现在拍的这部电影,可能没有人乐意去拍。”
回过分看,我也有遗憾的事。那时候我对韩国电影史的理解还不是那么深入,以是很可惜的是,2014年我去美国圣地亚哥的末了一晚,恰好有一个熟习的韩国教授出差到此,他跟我说晚上有一个派对,韩国最早的武侠导演郑昌河也在,你要不要过来?我那时不太知道这位武侠导演的历史影响力,结果错失落了跟他见面的机会。要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就被喷鼻香港邵氏兄弟影业聘请,双方互助12年,1972年他执导的《天下第一拳》在美国公映,创下新片票房排行榜第一的佳绩,这是有史以来非好莱坞电影在北美票房排行榜上的第一次胜绩,对喷鼻香港功夫片开拓欧美市场,意义深远。这事我想起来就会以为遗憾。
北青报:以外国学者的视角回顾韩国百年电影史,您采取了“代际划分”的办法梳理,这一方法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
范小青:在韩国学习期间,我的同学、前辈,还有教授他们跟我聊中国电影的时候,对中国导演张口闭口都是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乃至在2000年初期,对谢晋导演的研究在韩国大学的教室里也算是一个热点。这启示了我,让我以为对付不太理解韩国电影历史的细枝末节,但是又有理解冲动的影迷来说,这种代际划分的方法论该当是可行的。于是我就去找理论和历史的支持,我在韩国电影资料院里创造上世纪80年代的杂志,他们当时的电影评论家写到,韩国电影第三代旗手李长镐领导韩国电影史上最早的电影艺术运动“影像时期”如斯;后来又在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评论家著述的韩国电影史中创造了“代际”的用法,果真“代际”对他们来说也是熟习、认可的观点。
不过我认为只有电影人在电影圈的“代际”经历这一根支柱难免不稳定,出于这种自发的意识,我用创作世代和家其时期为经纬主轴,相辅相成表现韩国电影史的流变。我的老师李庸不雅观看了说,“一个韶光,一个空间,你利用电影的两大特色时空相连,写了一本电影史。”老师的话让我顿悟,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过!
看到他者的强大,看到自我的上风
北青报:您曾说,天时、地利、人和创造韩国电影的历史奇迹,这个中“386电影世代登场”是人和的表现,若何理解“386世代”这个观点?
范小青:所谓的“386世代”这群电影人,他们都是上世纪60年代韩国婴儿潮期间出生,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当他们30多岁时进入职场,把一腔热心投放到了大众文化当中。他们经历了很多韩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宜。也因此,上世纪90年代初崭露锋芒的电影制片人和“386世代”的大举登场,预示着韩国电影变革“人和”条件的成熟。
事实上,“386世代”不仅让本国不雅观众看到了本国电影的冲击力,让不雅观众自动走进电影院支持本国电影,而且“386世代”有能在商业上发力的,也有能在艺术上发力的,比如2019年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左手拿起金棕榈,右手拿起奥斯卡,他们让本民族的不雅观众看到了本民族电影所具备的视觉效果和情绪效应,同时在外洋发出了声响。
一个国家的强大自傲是通过文化润物细无声,韩国的“386世代”就担当起这个文化软实力的任务。比如李沧东导演,他曾经是韩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得遍了韩国的文学大奖,但他为什么在40岁的时候毅然决然放弃写小说转而投向大银幕?他说,“我看到了侯孝贤的电影,为什么侯孝贤良够把我心里的秘密说出来?”他意识到电影可以解脱笔墨的束缚,能够把他的想象力传遍天下,是找到他的读者的最便捷、最活色生喷鼻香的路径,以是他放弃了再用笔墨去跟人沟通。
北青报:在您看来,韩国电影是如何在环球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关注的?
范小青:在电影史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韩国人一贯是憋着一口气想要发声的。韩国电影崛起的一个主要缘故原由是他们看到了他者的强大,也看到了自我的上风。我以为韩国文化当中的一个分外的点,或者说韩国电影最能够打动人的都是他们把自己的薄弱呈现出来,跟希腊悲剧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先冲动自己,然后冲动他人。
韩国电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这个过程中他们阐发自己民族的东西是诚挚的,有人类共通的情绪,这点是非常主要的特质。他们首先类型化讲好故事,其次在讲好故事的同时,不会放弃问题意识和个性表达,这是它的文化含金量,以是它既被普通不雅观众认可,也被电影业界认可。
范小青和同学们
通过更多的电影节、文化活动,培养年轻一代的电影文化意见意义
北青报:请您谈谈值得关注的韩国女性导演,以及对韩国女性导演群体崛起这一征象的思考。
范小青:作为一个生活在韩国的中国女性,我很切实感想熏染到了“她力量”。这些文化女性不是依赖男性去得到威信感,她们完备是通过自己的专业水准,通过单打独斗得到认可。比如我打仗的“386世代”的女导演以及和她们年纪相仿的研究生院的前辈,她们目前都是各个大学的女教授或者是女学者,她们有共同的特色,比如她们都是短头发,不扮装,大多数是独身的,活得很爷们。她们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为了将来的女性在电影片场有一席之地,放弃了特殊多的“美满生活”。
但自从进入到韩国电影的“江南时期”之后,一个明显的变革是女性导演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明朗,虽然她们都还是拍一些低预算的电影为主,但是她们通过正视自己的女性主体,去表达有女性诉求的电影,去传播这种影响,我以为这是一个大的进步。
北青报:人们对电影的判断实在非常繁芜,您认为如何培养大众对电影艺术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见意义?
范小青:电影文化潮流特殊关键的一点,在于年轻一代的兴盛。以是我们要培养真的有电影审美能力、审美意见意义的年轻一代,就要有更多的电影节,有更多的电影文化活动,包括市民文化活动,比如像FIRST青年电影展,在青海已经举办了多届,既能勾引群众性的文化欣赏,同时又能调动文旅结合,像这样市民互动的活动每个省都能有一个,势必能带动文化鉴赏力、文化意见意义性,同时又能带动经济发展。那些受到大学生群体喜好的电影节,比如像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大学生电影节等等,这样的电影节在上海、广州、重庆、南京等大城市都可以多一些,通过文化放映活动去影响年轻人和普通市民,培养大众的文化审美和意见意义。
北青报:您在传授教化过程中感想熏染到当代大学生有若何的精神面貌?发展起来的年轻一代,他们如何建立文化自傲,实现文化出海?
范小青:我跟我的学生沟通蛮多的,他们也比较生动。但也有令人隐忧的点,现在的年轻人对人和人、人和社会的互换希望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至于说如何实现文化出海,首先心腹知彼,比如要理解和学习别人从“借船出海”到“出海造船”的策略。电影《寄生虫》有一组数据值得思考,截至2020年2月已经为韩国带来了1293亿韩元的直接经济收益,产生了7668亿韩元的消费品发卖和出口,带动了1.46万亿韩元的生产额,并新增了6399个就业岗位。2022年,韩国文化产品出口高达133亿美元,是2005年的10倍。从电影来说,我们是文化大国,讲好中国故事,一旦沉睡的电影雄狮醒来,必会与环球产生碰撞与共赢。
来源: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