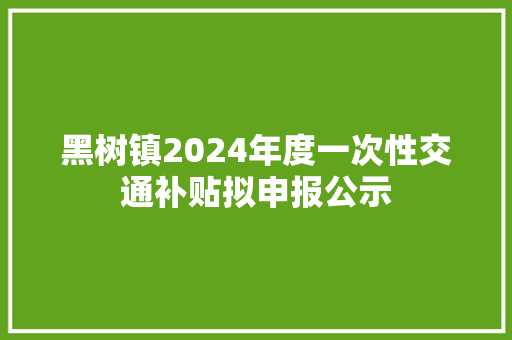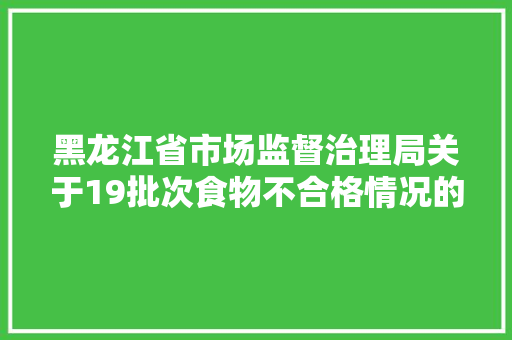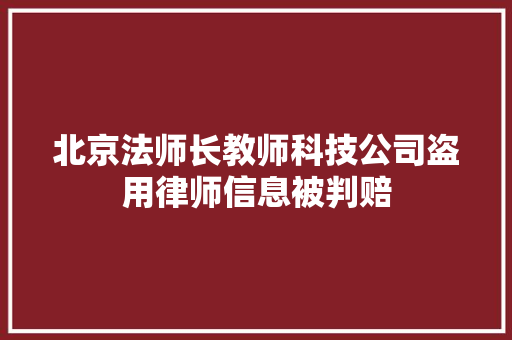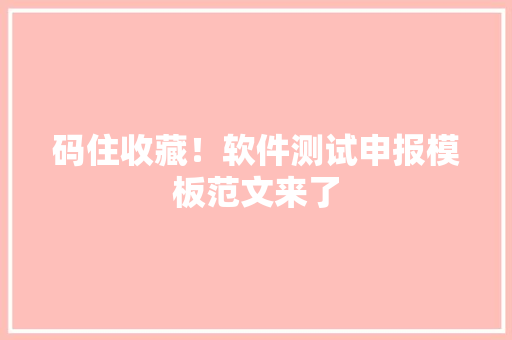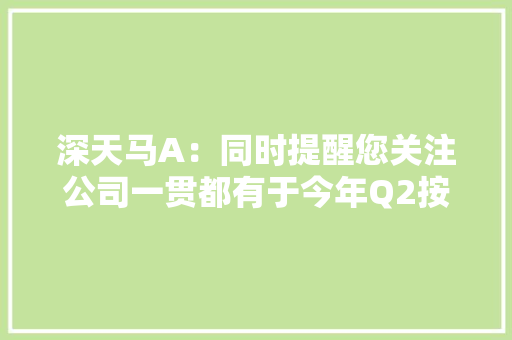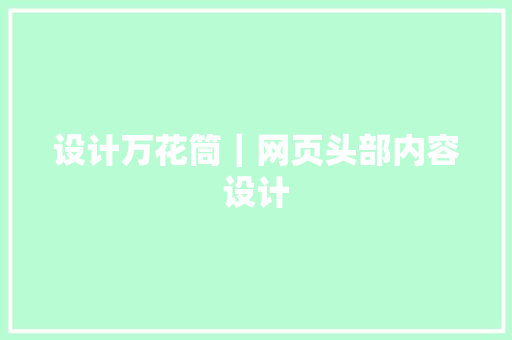BADHEAD第一击
1999年三月,摩登天空旗下坏头制作室同时推出“我快乐去世了”、“走失落的主人”、“大家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以及代理直接盛行苍蝇乐队的同名专辑,一举为中国地下摇滚的传播首创了先声。

212.我快乐去世了(B-001)

1999年,北京滚坛源源不绝地流溢出新兴的声响,声响的新兴并非旨在声音本身,更多表示在创作者的内在不雅观念和外在本色方面,并从根本上差异了97年以古人们曾熟习的京城摇滚印象,面对杂草众生的新声音,电气机器声响之美将中国摇滚拉入了后工业时期。
陈底里像京城的许多滚客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电脑,也习气起用电脑制作音乐了,已是此道高手。滚坛此时正陷入一个极度两极化的抵牾冲突情状,极度褴褛的乐队录音设备与时尚尖真个科技创作技能在无知不清的洪荒中搏斗,由此引开一扇毫无法则可以遵照与制约的电子之门。
“我快乐去世了”,仍是一张令普通人头疼的实验摇滚电子唱片。在烦躁不安的听觉困惑下,让人产生厌烦感情,继而彻底抵制的生理。底里的音乐实质是无罪的,电子领域硬软件数码的改造与环球多媒体规格制式的统一确立,是高尖科技声响物理工程的打破,所差的便是电子硬核这种风格还不被多数人认为是一种真正的音乐,但比较中国摇滚乐的初期制作,电脑编曲显然要比过去的仿照录音严谨很多。
《我快乐去世了》:出品人/江凌、沈黎晖 词曲/配器/演奏/录音/制作/陈底里 拍照/黄旭、孙达 发行/正大国际音乐音乐制作中央 出版/国际文化互换音像出版社
213.走失落的主人(B-002)
1993年夏天,左小祖咒来到北京,在倒卖打口磁带的过程中结识了夜千。夜千从小学钢琴,父亲是在中心音乐学院任职,他的选择却是与家人的希冀背道而驰。NO乐队的最初成员还有来自西藏的吉他手边巴平措和鼓手卢奇,初期的NO乐队于95年5月份终结。
1995年,方无行在做“赤地系列”的时候,本打算做祖咒的。祖爷儿那时气盛,向小方夸下海口,认为他的专辑在环球范围内至少能卖个几百万张,方无行以为他太狂,就把他赶走了。1997年,祖咒终于得到一笔帮助,随后订了个棚,在30首作品里选了9首凑成首张专辑,整张专辑的录音韶光仅为7天,直到1999年才得以面世。
经历了5年的煎熬,祖咒终于迎来了走失落的主人。在考试测验末了一次歇斯底里的治疗后,他呓语着,让我再见一次大夫,刀尖向内比向外须要更大的勇气,但他绝不愿去世在别人的手上。经他慎思严密出的乐段,皆可谓是对耳朵的颠覆,对本性的激活。他站在妖怪与天使之间,在保持个体纯粹的同时为人性歌唱。
《走失落的主人》:出品人/江凌、沈黎晖 监制/左小祖咒 录音室/北京寒塘音乐工作室 录音/马军 主唱/左小祖咒 吉他/虎子、祖咒、李延亮 贝斯/李剑、夜千 鼓/张蔚 拍照/三类人 发行/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央 出版/国际文化互换音像出版社
214.大家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B-003)
有人说胡吗个的音乐有点像张楚,事实上他们之间那一丁点儿的相似与他们之间诸多的不同比较,可完备忽略不计了。这个来自鄂西的年轻人,唱歌时操着浓重难懂的湖北口音,让我在聆听的同时要瞪大眼珠子盯紧歌词,稍有闪失落就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也有人评论胡吗个便是中国的鲍勃迪伦,尤其是在听那首“有人从背后拍打我的肩膀”这首歌的时候,在一把木吉他的大略伴奏下,他提着嗓子歪歪丫丫的唱,但也不过是形式上的相似,在歌曲的内容和境界上并不能相提并论。
显然胡吗个是喜好讲故事的,用一种直白的口吻讲着自己或是别人的事,但思路有些散乱,常常序言不搭后语。却也由于这种冲破了束缚的形式,让他的音乐走入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以是这是种打破。他用音乐勾勒出来自外省屯子的寄居者与大城市环境扞格难入的孤独感,在内心变与不变的纠缠中,用他所特有的非常规办法表达出来。
《大家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出品人/江凌、沈黎晖 拍照/罗勇进、胡渝江 发行/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央 出版/国际文艺互换音像出版社
BADHEAD第二击
215.MUMA(B-004)
木马乐队于1998年3月组建于湖南长沙,木玛(谢强)、曹操、胡湖分别是年夜夫、墨客和火车司机的儿子。成军四个月后,他们北上,与“舌头”、“秋日的虫子”等乐队散落租居在北京西北角一处叫东北旺的地方。
1998年底,在沈黎晖听了“木马”的部分录音小样后,决定与其签约。半年后,木马进棚录音,制作人是老炮骅梓。木马本想自己作,但录完第一首歌的时候,涌现了太多问题,于是沈黎晖派来了骅梓为木马供应技能方面的支持。骅梓紧张在录制过程中完成一些监听事情,并且在技能和履历上为木马把关,在录制中起主导浸染的还是木马自己。
木马对付青春的描述是灰暗和颓废的,谢强也承认他的青春期是在焦虑中度过的。木马的每首作品时长都不短,最长一首竟有18分钟。谢强迷恋律动性的节奏,在排练的过程中常日会忘了韶光,如果3首歌能够表达同一觉得,那就合并成一首,如此一贯排下去,不要停……
沈黎晖没指望木马的专辑能赚到钱,但还是坚持做出来了。谢强对付有名度的提升感想熏染不强,由于所谓地下摇滚明星的头衔并未为令他的生活得到实际意义上的改进,而是每搬去一个新地方,他都得积极地与小卖部老板混熟,由于只有这样他才能赊账。
《MUMA》:出品人/江凌、沈黎晖 监制/骅梓 录音室/正大国际录音棚 录音/李军 主唱、吉他/木玛 贝斯/曹操 鼓/胡湖 拍照/时小凡 发行/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央 出版/国际文化互换音像出版社
216.小鸡出壳(B-005)
舌头乐队的6位成员虽都来自乌鲁木齐,却均是汉族。因北京籍摇滚乐队在世纪末遭受到滑铁卢,以是令来自北京之外的摇滚乐队变得格外引人瞩目,并且“舌头”扬名的另一个主要缘故原由是受到了老崔的讴歌。
老崔说过,摇滚乐在中国就像一把刀子!
那舌头便是一把厉害的软刀子,由于它不仅是品尝食品的味觉器官和互换爱意的触觉器官,更是人类思想的通报工具。实在从第一次听到“舌头”的小样“复制者”开始,他们便在鼓噪的后朋克中跳跃着,锋芒毕露。
坏头品牌每张唱片的制作本钱掌握在大约2万旁边,这也令出版后摆进音像店货架上的专辑磁带的音质,并不比乐队早期自费录制出的小样强多少。因“复制者”的歌词没有过审,以是在唱片内页中无法涌现。听摇滚歌手唱歌,如果不看歌词,我实在听不懂他们在唱些什么。
在“小鸡出壳”硬核的外衣下,舌头既然不能以牙还牙那么就以嘴还嘴。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这些屡见于国内外滚圈的恶习,就算是初出茅庐的小鸡也将身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自已。在后朋克惨淡、病态,混着狡诈的乐风中,乐队用尖利刺耳的吉他音色,不怀美意地反复迂回着,贝司沉重,鼓厚重,键盘音的推波助澜让扭曲了的舌体在噪声的氛围里炙烤,并缓慢地发酵,那份愤怒与绝望的感情,已明白无误地被其表述了。
《小鸡出壳》:出品人/江凌、沈黎晖 制作/舌头乐队 录音室/北京电影学院录音棚 录音/黄浩 拍照/时小凡 主唱/吴吞 吉他/朱小龙、李红军 贝斯/吴俊德 键盘/郭大纲 鼓/李忠涛 发行/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央 出版/国际文化互换音像出版社
217.庙会之旅(B-006)
在“走失落的主人”录制后没多久,祖咒就在家里开始用八轨机制作第二张专辑了,“庙会之旅”的作品,一半新,一半旧,末了租了2天录音棚进行后期混音后,第二张专辑就完成了。祖咒无论是在弹吉他还是拉小提琴方面的成绩都是野路子,虽然93年,他初入北京时,也考虑过去学学别人弹弹吉他solo,但不久就演化成随便弹随便唱了。在录音乐手的选择上,祖咒也是喜好挑那种音色弹得不像吉他的吉他手,权友虽然鼓技出众,但却打不惯祖咒的歌,他对祖咒说,你的东西太邪门了。
祖咒的文学天赋不错,以是有些人虽不爱听他写出的曲子,但便是喜好那些歌词,他的小说《狂犬吠墓》也备受好评。祖咒认为自己的音乐不属于朋克,虽然他的现场听来也挺噪。
世纪末的北京滚坛迎来朋克时期,有像“新裤子”、“花儿”这种喜好傻乐,爱扮可爱,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的盛行朋克;也有像“木马”、“舌头”那样唯美、冷漠的后朋克。但是非北京籍乐队的崛起,并未代表彼时的摇滚乐已全国范围性的各处着花,而北京城依旧是中国摇滚乐所不可或缺的最大舞台。
《庙会之旅》:出品人/江凌、沈黎晖 制作人/左小祖咒 录音室/北京寒塘音乐车间 录音/祖咒、黄浩 拍照/李卫 主唱/左小祖咒 吉他/朱小龙、祖咒 贝斯/李墙 鼓/张蔚 键盘/郭大纲 合唱/吴吞、魏国 发行/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央 出版/国际文化互换音像出版社